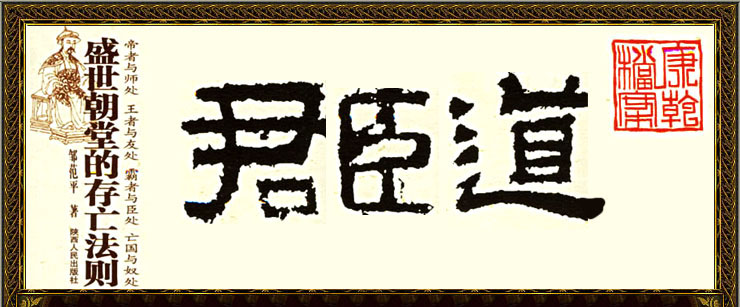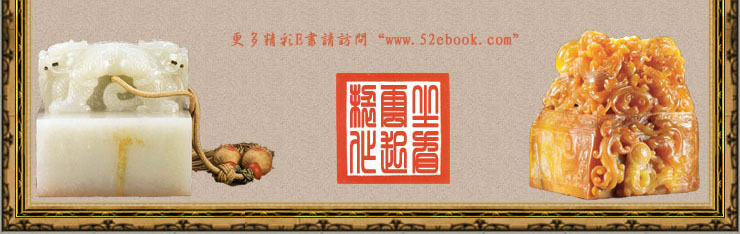因为顺治早死,康熙幼年即位,由四大臣共同辅政,鳌拜位居最末,却最为专横跋扈,摆在少年康熙面前的既是一个“吏治堕污,民生憔悴”的烂摊子,又是一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康熙帝
辅政大臣鳌拜的跋扈擅权,使得以贤臣辅政(或摄政)这种为儒家所倡导的好制度变了质,这本来是中国古代社会惟一具有进步意义的权力分配方式,也是原始儒家所追求的理想。这不是有没有制度保障的问题,而是由于人的素质低下,品质恶劣,败坏了好制度。这正应验了荀子所谓“有治人无治法”的观点。荀子说: “法不能独立存在,律例不能自动施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律是治的开始,君子是法之源头(源清则流清)。故有君子则法虽然有缺失,而足以周全;无君子则法虽具备,施行必然有所失,不能应事之变,足以导致乱局……故贤明的君主急于得其人,而昏暗的君主却急于使法律贯彻。”(《荀子·君道篇》)。康熙帝非常赞同荀子的观点,以为这是至理名言。
康熙帝整治鳌拜以后,学习汉儒文化,中国明朝的权力形式又被恢复了,所谓“清承明制”,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也有重大的遗憾。康熙帝为了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而抛弃满洲家法,成为古代中国最高文化利益的保存者,堪称大智大勇,然而失误也是如影随形。
康熙帝重新制定了治国方针。在“渐习汉俗”、“振兴文教”的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上,理学大儒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熊赐履、李光地、张英等帝师们的言教启发,使康熙帝树立了仁义的价值观念,促成了他在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成熟。理学对他的影响最有价值,人称“理学皇帝”。康熙帝以“与民休息”的政策为治国宗旨,这既是康熙帝深谙“戒急用忍”谋略精义的体现,也是理学“惟在躬行,不在口讲”之主张的实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