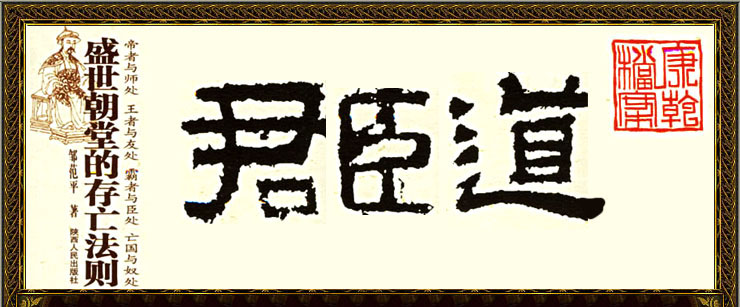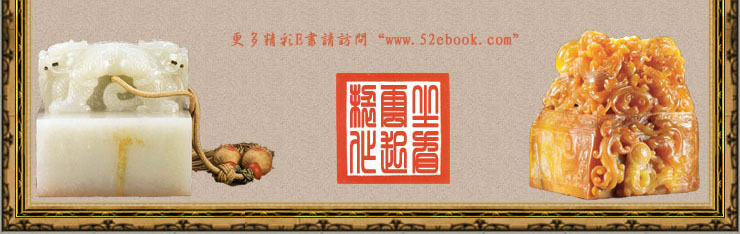前文说到,汉族大臣们不可能求得“冢宰”分权的地位,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求帝师的地位了。早期儒家都是以周公事业为理想模式的,唐宋时期士大夫还有“致君尧舜”的气象,就是在最昏暗的明朝,还有过一次张居正辅政,都是“冢宰”分权的先例。惟独到了清朝,皇权的旁落除了鳌拜擅权就是太后垂帘听政,都没有积极意义。在清朝初期,汉臣只有做顾问参谋的份儿,士大夫的地位低于满族家奴者,有时甚至连士大夫的尊严都保不住。
康熙初年,参与决策的除四大臣之外,还有议政王大臣、贝勒。这些满洲贵族大多对汉儒文化不以为然,其中孝庄太后的影响力也不小。她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偏爱,自然也是讨厌汉语、汉俗,认为“汉俗盛则胡运衰”,不赞成顺治帝和康熙帝学习儒家文化。但是也有人认为,孝庄太后是喜欢汉学的,康熙帝尊重儒学也是受到她的影响。这就矛盾了,然而历史常常就是这样不明不白的。可以肯定的是,康熙帝从小对汉儒文化就十分感兴趣,首先要归功于他身边的两位原明宫太监,张某和林某。二人原是读书之人,他们不仅教授他四书五经,书写汉字,而且经常给他讲述明朝的宫廷轶事和典章制度,使康熙帝幼年就对儒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幼年教养是何等重要。
儒家文化意识最重视教育兴国,对君主的教育尤其重视。虽然说是“君权天授”,但君德却不能不得之于学养。“天”与“德”也可以画等号,把权力赋予有德之人,是古人“尚贤”观念的体现。心术不正之人,一旦处于至高无上之尊位,必然会给国家带来巨大浩劫和灾难。自然灾难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坏皇帝的祸害深重,所以教育皇帝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大事。封建社会既然不能民选皇帝,就只有通过教育皇帝的途径来“选择”皇帝的贤愚。贤明的皇帝是通过道德教育这一选择方式产生的。其实,皇帝的权力是天赋这一观念的本意,不是指神权与皇权合一,所谓“天择”、“天授”,就是要讲道德,因为道德是源于人之天性(自然之性),人欲则是源于外界刺激。儒家认为,向善是人之天性。今人否认人之初性本善,也就会误解“君权天授”的意思。其实,天就是大公无私之意,“君权天授”就是要求皇帝大公无私。历代皇帝故意歪曲儒家的观念,掺入法家观念,后人就搞不清本意了。
康熙四年(1665年),太常寺少卿钱铤上疏,要求教授小皇帝儒学,他指出: “君德关于治道,儒学尤为急务,请将满汉诸臣中老成耆旧、德行温良、博通经史者,各慎选数员,令其出入侍从,以备朝夕顾问,先将经史中古帝王敬天勤民、用贤纳谏等善政,采集成书,分班值讲,每日讲说数条,不使间断,必能有裨圣德。”这在鳌拜辅政之期当然不可能实行,鳌拜所要的仅仅是权力,而非权力的道德化。权力说到底也就是人际关系,以什么为基础呢?以德为基础,抑或是以利为基础?《左传》说: “君能掌握天命为义,臣能承受天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宣公十五年)所谓“天命”也无非是规律的意思,以义与信谋利,就是符合天命,就是保卫社稷,可以做人民的君主。让皇帝学这些知识,鳌拜是反对的。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亲政,汉族大臣再次纷纷上疏,请求教授皇帝儒学,开设经筵日讲(即为研读经史而设的御前讲席),这些建议仍然没有被辅政大臣们采纳。在他们看来,满洲是从马上得天下,如今以马上治天下,乃是顺理成章,满洲皇帝只需精通骑射,所要学习的也只是“满洲家法”而已。后来康熙帝剪除鳌拜,抛弃清朝“祖宗家法”,“悉承明制”。令人遗憾的是,“祖宗家法”中的积极因素也被抛弃了,“悉承明制”却是把明朝的消极因素加强了。
在封建社会,汉族皇帝或皇太子的教育向来受到特殊的重视。汉朝贾谊说: “天下兴亡,悬于太子之手,太子善恶,皆在于少年所受师傅的教育和周围人的影响。”康熙帝后来又为皇子们规定了学习制度,皇子6岁必须读书。以后雍正帝把它作为一条制度固定下来,正式设立上书房,以总师傅、总谙答为首的教育管理系统。自古以来,帝师往往是由名重一时的硕彦大儒来担任,称太傅、太保。不仅是为了小皇帝和太子的教育,成年皇帝的教育仍要照常进行,学习内容从文史知识转为探讨治国之道。对于成年皇帝,师傅又称为侍讲、侍读或经筵日讲官,如宋代的程颐、朱熹、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做过经筵日讲官。经筵为盛典,每月三次,平时则不定日进讲,以收持之以恒的效果。皇帝选官以才能和道德为标准,“以臣选君”既然不行,以道德塑造君主就是惟一的办法。
在促使恢复经筵、日讲制度这件事上,弘文院侍读熊赐履起到了重要作用。
熊赐履(1635~1709)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顺治进士,东阁大学士,居官清廉敢于言事。康熙六年,他上著名的《万言疏》,列数朝廷上下存在的种种弊端,特别指出教育皇帝是建国之本,“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薰陶德性。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读书。不徒然从事讲读之虚文,不徒然虚应经筵之故事,不以天气寒暑而有停辍,不以日夜晨夕而有间断”。帝师的作用初步表现为教授小皇帝基本的文化知识、道德修养,而且有很明确的目标,是为了“行政出治”。同时注重民间教育,如今“学校极其废弛,士子惟揣摩举业,为掇取科名富贵之工具,不知读书讲学是求圣贤之道理。乞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则道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中国古人有“仕必由道”的观念。创立科举就是为了使“以道取仕”有一个标准,然而读书人大多都把科考与富贵紧密相联系,却与“圣贤道理”远离了,入朝为官,鲜有不做贪官者。
熊赐履提倡讲学以明了道理,这是做官的基础。与做君的基础一样,君臣都是同一个基础,这是儒家的君臣观,如臣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立君为民,无为;君以道驭臣,纳谏等等。法家君臣观念则不然,讲的是君势、法术一类的关系。一般来说,君主所注重的都是法家观念,熊赐履要求康熙帝学习儒家观念。
次年,熊赐履又上《清除积习销隐忧疏》,“皇上聪明,而朝纲独断,讲学与勤政二者不可偏废”。熊赐履两次上疏均遭鳌拜斥责。康熙帝受到鳌拜的压抑,对于权力分散的满洲家法十分厌恶,立志要朝纲独断,以儒学为治国经纬。从此,“满洲家法”中的积极因素被否定,而汉文化中的法家毒素却被发扬光大了。“朝纲独断”与其说是儒家的思想,倒不如说是法家的思想更确切。
在擒拿鳌拜一个多月之前,康熙帝采纳汉官建议,亲自到国子监去祭祀孔夫子。皇上亲自祭孔,这是一个象征,表明清王朝与中国历代王朝一样,尊孔崇儒,孔孟之道仍然是中国人的正统思想,这既起到了笼络汉族官民的作用,也给清王朝的统治增加了合法性,因此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一个月以后,康熙帝剪除鳌拜及其势力,满洲贵族中的仇汉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康熙帝立即着手施行经筵日讲制度。
康熙九年(1670年)七月,康熙帝召国史馆学士熊赐履到瀛台试讲。熊赐履进讲《论语》“道千乘之国”一章,继讲“务民之义”一章。康熙帝听后,感到哲理深奥,切中事理,大有所获。
十月,康熙帝命改内三院为内阁。内阁之制始于明代,其所以名之“内”,是因为“以其授员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是统率百僚“行政总汇”的封建官僚政治的中枢机构,协助皇帝治理庶政,商议朝政,传宣御旨,而内阁大学士称为“枢臣”、“相国”。内阁地位在六部之上,首辅虽无宰相之名,却被人们视为宰相。又重设翰林院,并选择翰林数人入值内廷,以后又设立专门供皇帝咨询和顾问的南书房。
康熙十年(1671年)二月,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经筵典礼,由工部尚书王熙和熊赐履分别进讲。此后,每年春秋两季照例举行。经筵讲官都是由皇上慎选的德才兼备的学问优长之士,如熊赐履、王熙、吏部尚书黄机、刑部尚书冯溥、都察院左都御史明珠等,此后这些讲官便担任大学士,所谓“以大儒为名臣”,即以帝师为大臣。日讲地点初在弘德殿,后移乾清宫。讲官由翰林院官员担任,有熊赐履、史大成、李仙根、张贞生、严我斯、蔡启尊、孙在丰、杨正中、杜臻、张英、沈俭、史鹤龄、陈廷敬等,还有满族学官折库纳、傅达礼、莽色、喇沙里等。从此,清代帝王的培养、教育制度得以制定完备。经筵日讲的恢复有重大意义,满洲皇帝学习汉儒文化必然对帝师由尊重信任而重用。康熙帝说: “朕政事之暇惟好读书,始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乐此不倦。继而张英、陈廷敬以次进讲,于朕大有裨益。”
一般人学知识,多为谋生之资本。既然是皇帝,“我要什么就是什么”,何必学知识?儒家认为,学习的最高目的不为谋生而为修身。贵为天子当然须求学习最高目的之实现,老百姓也就有福了。此时,康熙帝作为十七八岁的青年,正是嗜欲日开之时,他把精力用于治国,尤能勤奋治学,确是十分难得。康熙帝的学习精神不仅使那些庸碌懒惰、淫乐无度的明朝皇帝黯然失色,也使那些专为科举考试而读圣贤书的汉族士人相形见绌。他五更就起床读书,常常读到深夜,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也不休息。汉儒文化对这位年轻的皇帝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多年的苦读精修,为康熙帝以后的治国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使刻苦学习成为传统。以后,雍正帝、乾隆帝等清代皇帝都是从小就刻苦学习,这是其他朝代的皇帝无法相比的。
清代宫廷内,有两个书房。一为上书房,是皇子受师读书处;一为南书房,是皇帝研究学问处。故宫的乾清宫之西为懋勤殿,是康熙帝读书处。南面的乾清门右阶下是“内廷词臣值庐”,因其位置居懋勤殿之南,故称南书房,是康熙帝与入值翰林院探讨学问的地方。这些人基本上为汉人,最重要的作用是顾问。
从康熙帝开始,满汉矛盾确实已降到次要地位了。满汉君臣关系中的文化矛盾,至少在表面上被掩盖了,从本质上也被稀释了。如果实行满洲家法,八王共治,汉人也是没有决策权的。两种权力分配方式都对大多数中国人不利。满汉两种“家法”孰优孰劣呢?正如不可以把生长于沙漠中的胡杨柳与生长于江南水乡的垂杨柳相比较而定优劣一样。我们只能说,适应具体的客观环境的某一种柳是好的,不适应就不好——不论是旱死或涝死。古代的君臣关系是当时客观条件的产物,关系和谐,老百姓就过好日子;否则老百姓就遭殃。历史选择了汉人的“家法”,至少可以避免发生内战。满洲家法的形式不适应大一统的中国,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却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一致。这真是一个悖论。正如鳌拜与周公从形式上说都是好的,但是个人修养不同,结果就不同。中国古人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关系其原因在此。借用鲁迅的话,“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例”: 在西方历史上,德国人民把希特勒选上台,造成人类大劫难,就充分证明了制度好坏不是根本,人的好坏才是根本。修身与治国的因果关系是不可以颠倒的。君主制的形式可以改变,做好人的观念永远不可以变。至少,在无法直接改变某一种制度的历史条件下,求其次,提高君臣的道德,总是于老百姓有好处的。中国老百姓要好皇帝和清官,并非是愚昧,因为历史条件的改变非数十年或百年之功不可以成就。
历史不能不走“弯路”。清朝初年,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为代表的激进儒学,在清廷文字狱的高压之下,无法取得主流的地位。因此,只有承认既成政治现实,与朝廷合作的士大夫及其尊崇的理学,才能成为儒学主流,这一派儒学所起的作用,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它的功绩在于改造了清政权的落后野蛮性质,缓解了满汉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安定了战后的社会秩序。可以说南书房的帝师们为清初盛世做出的贡献是极大的,其功不可没。
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刚正不阿,以道事君,是康熙帝最为信赖的一位帝师。康熙帝说: “朕初立讲官,熊赐履早夜惟勤,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讲论,务得至理而后已。”通过与熊赐履的反复论讲,康熙帝的涵养功夫不断深化,确是大有益于治国。及至晚年,康熙帝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曾说: “朕自幼读书,略观经史,知道持身务以诚敬为本,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虽德不厚,性不敏,而此心此念兢兢持守五十年,未曾间断。”
康熙帝从熊赐履的讲论中得到的最大的教益就是“中庸之道”,对其用人行政都有极大影响。对于“中庸之道”,今人多有误解,以为不过是中立,或调和,不知“中庸之道”乃是智谋的极至,表现为公正无偏,大智若愚。康熙帝在用人上的中庸之道,体现为强调廉与能的结合,虽然他很强调清廉,但是只“廉”而不“能”者也不用。他说: “督抚为地方大吏,操守为要,才干为用。大法而小廉,百姓则俱蒙福矣。为官不可过于贪婪,亦不可过于廉刻。过于廉刻则不能和平宽宏以率下,操守虽清却不利于办事。只有既廉洁又能行有益于地方民生之事者,才堪委任。”这就是中庸之道。
熊赐履治程朱理学,主张默识笃行,穆然清静,治国以宽缓平和为善,严猛繁苛为不善。康熙帝深受其影响,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几乎贯穿于一切政务之中。康熙帝非常理解与民休息的政策并非权宜之计,而是长治久安之策,并始终遵守着这一治国方略。
君臣常常结合时政探讨理学问题。有一次,熊赐履进讲之后,康熙帝问他: “近来朝政如何?”熊赐履答道: “奢侈荒怠至今日极矣!官贪吏酷,财尽民穷,种种弊蠹,皆由于此。皇上励精图治,明令严禁奢靡,崇尚节俭,人人皆以为当今第一要务。而有司视若虚文,奉行不力,但恐积习沉痼,猝难改移。惟在皇上躬行倡导,加意剔除恶习,太平无疆之业,全在于此。”康熙帝又问: “从来治国在安民,安民则弭盗。如今外面盗贼稍息否?”熊赐履答道: “圣谕及此,是天下生灵之福。臣阅邸报,见盗案烦多,朝廷设兵以防盗,而兵即为盗;设官以弭盗,而官即讳盗。官之讳盗,由于处分之太严;兵之为盗,由于月饷之多克扣。今日弭盗之法,在足民,亦在足兵,在察吏,亦在察将。少宽缉盗之罚,重悬捕盗之赏,就可以了。”康熙帝深表赞同: “诚然。”一般来说,忠臣对英明的皇帝总是报忧不报喜,如果大臣报喜不报忧,英主就会认为他是佞臣;反之,大臣对于昏暴的皇帝则报喜不报忧。问题不出在大臣身上,主要是看皇帝的喜好而定报喜或报忧。康熙帝、雍正帝比较喜欢大臣们报忧,乾隆帝比较喜欢大臣们报喜。
康熙帝对熊赐履十分依赖,频繁召对,言听计从,深为信任。所讨论的内容也极为广泛,凡诸子百家,国计民生,用人行政,无所不论。康熙十四年,熊赐履升内阁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
一次,君臣讨论不扰民的问题。熊赐履说: “为治固患废弛,然而求治甚急,将更纷乱丛生,必然困扰百姓,弊端丛生,所谓欲速不达。求治太急,还是人欲用事,必须无欲然后可以言王道。”官员以多事为政绩,以喧嚣为繁荣。急于用事者,不仅仅是欲速则不达,而且是欲留名则不达。康熙帝极赞成他的观点,以为清静无为之道确是治国的上策,“致治实在是不宜太快,只须日积月累做将去,久之自有成效”。一想到从朝廷到地方,那些日思升迁、亟亟乎建立丰功伟业的官吏们,他就摇头叹气: “从来与民休息,其道在于不扰民,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
康熙帝特做一篇《宽严论》阐述他的治国理念,他认为: 天下大治之本在于宽仁,这是上天爱民的体现。康熙帝要求自己“不多生事,但穆然清静,处之以和平”。宽仁、不事苛求,施教安民;和平,不事喧嚣,清静无为,行事太平,才有盛世。康熙帝读史书,见汉朝发生灾变即诛宰相,感叹道: “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倘有失误,君臣共之,竟然归罪于宰相,或有的君主,凡事都托付宰相,此君主之过,不得独归咎于宰相也。”
康熙帝常常要求督抚大员用人行政之时“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务以安静为善”。有一次,康熙帝对新任职的进士们谆谆教诲道: “士子读书稽古,原本期望穷理致用,平日砥砺廉洁,敦修品行,皆为异日服官莅政之本。等到一登仕途,志在功名,未免专意求进,干营奔竞,丧其素怀者往往有之。你们多从田间来,才通仕籍,务要率其平素行履,不改初心。凡受内外职任,当益加勉励而行,情操自矢,恬静寡营,循分尽职,洁己爱民,以副朕造就人才之至意。”
使汉人传统的意识形态仍然在大清帝国起着推动历史的巨大作用,熊赐履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一个大国若要国泰民安,传统文化的延续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汉儒文化虽然有许多荒谬之处,但是在明末那种世俗文化泛滥,而招致国家灭亡的悲剧之后,汉儒文化在异种称王的清朝又重新发挥了拯救世道人心和扭转社会风气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很值得深思的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康熙帝以宽仁著称,除了天资的成分,受益于帝师熊赐履的指导不少。就这一点来说,熊赐履对康乾盛世的贡献比其他汉臣都要大。这是人臣治国的大手笔,不是一般的智谋权略可以相提并论的。论智谋,熊赐履却不高明,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得很拙劣,大大有损于他的清誉。
康熙十五年,熊赐履犯了一个错误,因票拟出错,欲委过于人,改写草签,撕去嚼毁,失大臣体,被革职,迁居江宁(南京)。熊赐履虽然官拜大学士,但是家中竟然毫无积蓄,在江宁清凉台寓居时,清寒度日,与童仆一同锄地种菜。他自号“清凉老圃”,有时遇到青黄不接,往往“数米粒而炊,杂以野菜”。康熙帝南巡,接见他,赐御书匾。二十七年,起用为礼部尚书,仍值内廷,后调吏部。三十四年,其弟熊赐瓒因事下狱,御史趁机弹劾熊赐履,说他窃道学虚名,负恩溺职,请予严惩。都察院议欲降三级调用。康熙帝置之不问,并赦免熊赐瓒。三十八年,授赐熊赐履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以及《圣训》、《实录》、《方略》、《明史》等书的总裁官。
康熙帝对熊赐履教授辅弼之功,一直感念不忘,常说: “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熊赐履退休之后,仍然食俸,留住京师以备顾问。熊赐履去世之后,康熙帝命礼部官员前往视丧并赐银千两,赠太子太保、谥号文端。又眷念其旧劳,擢用其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