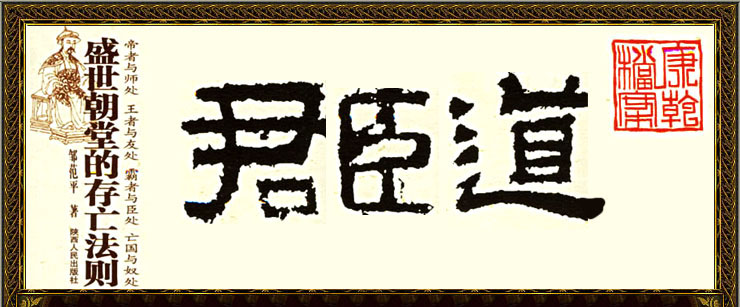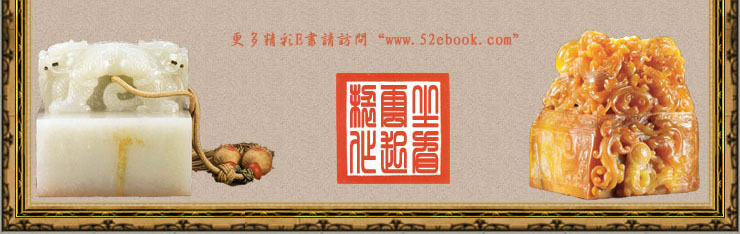康熙帝的统治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刚柔兼济,恩威并用。他既首重满洲(利益),又崇尚理学;既兴文字狱,又尊儒兴学;既坚持君主专制,压制整肃汉臣,又允许汉臣说话,以中庸之道寻求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强盛。
熊赐履久居官场中,迷恋权势,最后也难免沾染许多恶习。这里把他最著名的嚼签子丑闻揭出,使人知道,害人之道德最深者,无过于官场。
吴三桂之乱时,内阁大学士们常常错批奏章,朝议罚俸。康熙帝都免了,说: “他们心乱了,本无大事。”当时冯益都、李高阳、杜宝坻与熊赐履同在内阁,熊赐履有一次偶然拟批错了一件,被皇上检出来问。熊赐履颇心动,次日五鼓,便先到内阁,叫中书拿奏本来,又支走中书,找出自己错的签子(批答小票)嚼了,因见杜宝坻平素糊涂些,就裁去他别本一条批签,把自己错批的文字易书此于上。
等到杜宝坻来,熊赐履迎之说: “老先生昨天又错批了本了。”没想到这日杜宝坻却又精明,立即取本看,自己摇头作色说: “学生不曾见这个本。”熊赐履说: “老先生忘记了,不是你是谁?”杜宝坻又审视一遍,说: “昨日不曾见此,是何缘故?”厉声呼中书林麟焻至前,骂道: “我不曾见此本,都是你等作弊,我要启奏,先夹起你来审。”林麟焻大惧,跪下表白: “与中书不干,中书为何作弊?”杜宝坻问: “为何这一条签独短些?”林麟焻说: “不知道。”又问: “这一条是你的字么?”答: “不是。”问: “别签是你的字么?”答: “是”。杜宝坻说: “这必定有弊了。”
索额图在旁边有所知觉,说: “这容易,查昨日几本、几原签,即可知是谁错。”查少一原签字,问熊赐履。熊赐履忿然说: “这样难道原是我作弊不成!”
彼此喧争起来,大学士觉罗沙麻出来说: “熊阿里哈达何苦如此?某今夜在亲戚家丧事守夜,过来得更早,在南炕上倒着,看见阿里哈达检本,口内嚼了一签子,如何赖得?”
熊赐履语塞,索额图遂必欲启奏。众劝不止,索额图拉杜宝坻竟启奏,康熙帝命交吏部审问。以明珠为首的大学士们都到场,熊赐履不出一语,只说: “公等如何落供,即如何,某无可说。”
索额图说: “这本无大事,就是审贼犯,也毕竟要他自己亲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熊赐履仍不语,索额图又说: “老先生不要怕,就是如今吴三桂、耿精忠自己说出真情来,皇上也只得歇了赦了他,何苦不言?”窘辱备至。最后说: “罢了,就是如此罢了。”
为了这件事,熊赐履也就被落职回籍。康熙帝也不好袒护他,但以后又加起用。
明珠结党营私、贪赃弄权,声名狼藉,康熙帝也有耳闻。有一次康熙帝旁敲侧击地对明珠说: “如今做官像于成龙那样清廉的人非常少,做十全十美的人确实很难。但是,如果把‘性理’一类谈修养、正人心的书多少看一些,就会使人感到惭愧。虽然人们不能全照书上说的那样做,但也应勉力而为,依理而行才好。”
康熙帝总是告诫官员们要“存理遏欲”。他说: “大凡人衣食可以自足,便应知足,理应洁己守分。”又说: “洁己操躬,臣子之意,财悖入而悖出,古训所戒,子产象齿焚身之论最为深切著明,当官者宜铭诸座右。”“财悖入而悖出”一句,出于《大学》,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钱财来的不明不白,去的也不明不白。《左传》曰: “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因为象牙珍贵,所以招致毁灭。大臣如果过于聚集钱财,也会招灾。
小于成龙颇有胆力,他为官清廉,很得到康熙帝的信任,授直隶巡抚。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谒东陵,于成龙陪驾,向皇上揭发了朝廷的弊病,说: “天下官尽被卖完了,没有一个巡抚、布政使不是用钱买的。”康熙帝愕然,问: “何致如此?有何证据?”于成龙说: “皇上但使人将各省藩司库盘一盘,若有一处不亏空,臣便认虚妄之罪。他将藩库银子买升巡抚,藩司焉敢发其奸?相习成风,都是用皇上的钱买皇上的官,岂不可惜?”康熙帝又问: “是谁卖?”于成龙答: “不过是满、汉宰相,还有何人?”
所谓满汉宰相就是明珠和余国柱,清朝虽然承明制不设宰相,但是总要有俗语所谓的“领班”之人,视同宰相。明珠是满洲领班,余国柱是汉人领班。于成龙敢于揭发宰相之奸邪,大约也是因为明珠在治河的问题上支持靳辅的意见,与皇帝的意见相左,使康熙帝十分生气,此时揭发明珠的罪行,胜算的把握比较大。明珠之贪赃枉法,康熙帝尚能容忍,而他在朝廷内外交结朋党,在某些事情上藐视君主的意见,就不能容忍了。
回宫后,康熙帝又向高士奇询问,有关明珠卖官之事,可是真的。高士奇也说是真,然后将他们许多营私舞弊之事详细汇报一通。康熙帝问: “何以无人参?”高士奇答: “谁敢?”康熙帝说: “满洲不敢,汉官何惧?”高士奇说: “汉官独不要命吗?”康熙帝说: “有我。他们势重于辅政四大臣吗?我欲去则竟去之,有何怕?”高士奇答: “有皇上做主,有何不可呢?”
高士奇把康熙帝的意思向徐乾学说了,二人商议一番。徐乾学草书弹章令佥都御史郭琇奏上,又令刘楷、陈世安各上一疏,弹劾明珠、余国柱。高士奇先将他们三人的疏稿交给康熙帝过目,说: “郭琇早已俱稿,但迟徊不敢即上。”康熙帝改定几个字,说: “即此便好。”
第二天他们的奏章就上了。事前,风声已露,余国柱找到陈世安打听,说: “风声甚恶,听说你要上疏参我,确有此事,有何来历?”陈世安反问: “老师信吗?”余国柱说: “我正心疑,故来问君。”陈世安叹息说: “小人如此喜欢挑拨离间。我受老师大恩,豢养无所不至,哪里敢做如此的负心事呢?说这话的人,太不通情理了。”其实,陈世安是受到大学士索额图的指使。
余国柱释疑,放心去了。次日,弹章奏上。余国柱在内阁迎着陈世安,持其手扯至一边,问道: “听说有参疏上,可信吗?”陈世安说: “有。”余国柱问: “参谁?”陈世安说: “参的便是老师。”余国柱问: “谁参的我?”陈世安说: “人甚多,就是门生不得已亦在其内。”
余国柱大惊失色,震惧之下,已不能自然行走,距离内阁不过几步之遥,他手扶石栏杆一步一步,半天才移回到内阁。他平时胸中只有名利,紧要关头自然没有从容不迫的态度了。
郭琇的《特纠大臣书》共八款,摘录如下:
“一、凡阁中票拟,俱由明珠指麾,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皇上圣明,时有诘责,乃漫无省改。即如御史陈紫芝参劾湖广巡抚张汧疏内,并请议处保举之员,皇上面谕九卿,应一体严加议处,乃票拟竟不之及,则保举张汧原属明珠指麾,即此可见矣;
“一、明珠凡奉谕旨,或称其贤,则向彼云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云上意不喜,吾当从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结党群心,挟取货贿。至于每日启奏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
“一、明珠结连党羽,满洲则有尚书佛伦、葛思泰及其族侄侍郎傅拉塔、席珠等,汉人之总揽者则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向时会议会推,皆佛伦、葛思泰把持,而余国柱更为之囊橐(收容包庇),惟命是听,但知戴德私门矣;
“一、凡督抚藩臬缺出,余国柱等无不辗转贩鬻,必索及满欲而后止,是以督抚等官遇事朘剥,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逢圣主,爱民如子,而民犹有未给足者,皆贪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也;
“一、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后,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请价(请问价钱)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任意派缺,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方取贿,士风文教因之大坏;
“一、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皇上试察靳辅受任以来,请过钱粮几何,通盘一算,则其弊可知矣。当下河初议开浚时,彼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辞。及见皇上欲另委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举出必当上旨。而成龙官止臬司,何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于是一力阻挠,皆有倚托大臣(明珠),故敢如此。天鉴甚明,当洞悉靳辅累累抗拒明诏,非无恃而然也;
“一、科道官内升出差者,明珠、余国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即与之订约,凡有本章,必须先行请问,由是言官多受其牵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见人辄用柔颜甘语,百般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当佛伦为总宪时,见御史李兴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震方颇有弹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以上各款,但约略指参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窥探上旨,其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余国柱奸谋附和,负恩罪极,伏冀立加严谴。”(蒋良骥《东华录》卷一四;《清史稿》卷二六九,《明珠传》)
皇帝要大权独揽,无奈精力不济,必须要大臣参与决策。皇帝的旨意就在大臣票拟时被歪曲或阻挠。票拟不可避免地要被权臣掌控。明珠指挥“票拟”,操纵部院,暗中左右康熙帝的意志,在任免官吏时从中“展转贩鬻”、“图取货贿”。其实,卖官索贿,也不仅仅是为了积累财富,更是为过足官瘾,也就是把自我意志最大限度地发挥和运用。这是人类的通病,一入官场,此病就恶性膨胀。每个官吏在潜意识里都是皇帝。所以古人对治此病的良方只是自我修养,清官必然是人性自觉的表现,不可能是制度的产物,什么样的制度也治不了此病。
康熙帝对权臣明珠、余国柱倒很客气,只是降职了事,没有对之深究严谴。大约宽容也是运用权力获得快感的一种方式。有些皇帝非虐人杀人不痛快,而康熙帝以宽容为乐,其心理基础,可能要追溯到康熙帝对理学的体认。而御史们的心态就不同了,他们看到官吏们被整肃,纷纷落马,就高兴。所以总是要求严惩,以此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高士奇、徐乾学顶替了明珠、余国柱位置,郭琇升左都御史。其实徐乾学也是大贪官,更是一位野心家、阴谋家。过了一些时日,他见到高士奇较自己更受皇上信任,就妒火中烧。他也要做权臣,一旦驶入这条轨道,就无法停止弄权收钱的运作,总是妄想把自己的意志充分发挥,所有贿赂都归一己,皇帝对自己言听计从。时人说: “徐健庵(乾学)势倾满汉,高澹人(士奇)呼吸风雷”,“直至徐复谋高,而始两败俱伤矣”。(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一三、卷一四,《本朝时事》)
康熙帝又将南巡,徐乾学料定皇上到了南京一定要召见罢官后侨居南京的熊赐履。徐乾学企图把熊赐履拉回京,一起攻击高士奇。他派家人事先到熊赐履处传话,说皇上不喜欢的人,有高士奇、李光地、王鸿绪,皇上喜欢的人是徐氏兄弟等等,嘱咐熊赐履顺着皇上的意思说话,推荐皇帝喜欢的人,排挤皇帝不喜欢的人。康熙帝到了南京,果然就召熊赐履谈话,问到朝臣的优劣,熊赐履就按照徐乾学的意思说话。
康熙帝问: “李光地学问如何?”熊赐履说: “一字不识,皆剿窃他人议论瞎说,总是一味欺诈。”康熙帝问: “听说他晓得天文历法。”熊赐履说: “一些不知,皇上试问他天上的星,一个也认不得。”熊赐履又称高士奇、王鸿绪招权纳贿,奸滑诡诈,荐徐乾学道德、文章、经济兼而有之,古无其匹。
在南京,康熙帝特意试验李光地天文知识,觉得不是那么无知。又向高士奇询问: “李光地的学问如何?”高士奇答: “不相与,不知。”高士奇已经料到熊赐履在皇上面前诋毁李光地,而皇帝现在正在考察,又不知皇帝的态度如何,所以不敢轻易说好说坏,只是模棱两可。康熙帝说: “岂能全不相见?毕竟有所闻。”高士奇说: “相会也相会,但是不深相与,如何知道他学问?但看来自是读书人。”康熙帝又问: “不然。熊赐履说他一字也不通,且为人奸伪。”高士奇说: “是吗?这却看不出,或者福建人见闻短浅,则有之,若说一字不通,恐怕也太过分。或词章之学非其所长,倒是读些有根底书,也还算读书人。”康熙帝说: “你说话公道,到底是读书人。张英也如此说。”又说: “不特他,也有人说你不好哩!”高士奇明白一定是皇上听了熊赐履的谗言,但佯作不知,说: “臣学问很不成,学问、诗文何尝有胜人处?圣恩容恕,姑留在此,臣实无知。”康熙帝说: “却不是说你学问。倒说学问还好。”高士奇说: “然则说什么?岂说臣犯皇上法吗?”康熙帝说: “恐是如此。”高士奇故作不解状,惶悚而已。康熙帝说: “你也要提防。”高士奇说: “臣与人无怨无争。”康熙帝说: “总是要提防。”做皇帝的能如此关照大臣,已经非常难得。由此也可以看出康熙帝的仁慈。
回到北京,徐乾学见到高士奇脸上不悦,心知肚明。他又唆使郭琇参高士奇、李光地、王鸿绪,并亲自属稿交给郭琇。高士奇马上就知道了。在送孝庄太皇太后灵奉安到梓宫的时候,高士奇扯徐乾学到僻静处问: “老师何为做此事?”
徐乾学仰天叹气,发誓说是被小人诬陷,挑拨离间至于此极。又拉着高士奇的手,找来郭琇对质,说: “真奇怪,刚才高老先生忽然说我做疏稿,令你参他。今郭君在,老先生试问之。”
郭琇说: “学生今日至此,谁之力也?当日参明、余,非老先生左右,学生焉得至总宪(左都御史)?天下容或有为负恩之事者,然何为至此?真狗彘不食其余矣!”他们都说决无此事,高士奇将信将疑。高一走,徐乾学就握着郭琇的手说: “事情紧急,先发者制人。”
次日,郭琇的弹章就递上去了。参五人: 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王九敬、何楷,并要求立正典刑。然而,高士奇早有准备,事先得到奏稿,交给康熙帝。既然皇帝事前就提醒过高士奇“要防备”,现在也就不可能重谴高士奇,只将其罢官,让他在南书房修书。
有人曾在康熙帝面前揭发南书房侍讲高士奇,说他当初肩破棉被入京应试,现在只要问他有多少家产,就可知道他利用权力收了多少贿赂。其实康熙帝对此早已知悉,却不追究。他说: “诸臣为秀才时,谁不是布衣步行?一旦做了官,便高轩驷马,前呼后拥,这些钱都是哪儿来的,可以细究吗?”
在封建社会,御史的监督是否起作用,常常要看皇帝的好恶而定。康熙帝对高士奇等人的纳贿睁一眼闭一眼,到了乾隆朝,和珅公然纳贿,富可敌国,御史也参劾过,如果不是受乾隆皇帝的变相保护和鼓励,根本就不可能参不倒他。问题并不在于“下情不达”,而在于“上情不明”。到底是贪官好,还是清官好?皇帝喜欢哪一个?永远是一个问题。而且,在人治社会也不可能搞“高薪养廉”,所以御史赵璟的意见就没有被康熙帝采纳。皇帝不是最怕大权旁落吗?如果把权臣的纳贿与揽权看做是互为表里的一体两面,皇帝就不会纵容大臣收受贿赂了吧?不知为什么皇帝看不清两者的逻辑关系。
当然,总体上来说,康熙帝还是要抑制腐败、提倡廉政的,他的吏治方式是以优待清官为主,革除恶吏为辅,正面鼓励是其特点。雍正帝则正相反,他实施“以猛治贪”的政策,力纠康熙帝之偏,这两种治术的不同虽然与个人性格有关,但主要还是由当时的形势和皇帝本人对问题的认识有关。乾隆帝就比较纵容贪官,他不是像康熙帝那样出于宽仁的性格,而是讨厌批评朝政的清官,鼓励报喜不报忧的贪官。由于乾隆帝的吏治方式大不同于康熙帝和雍正帝,吏治遂腐败不堪。到了嘉庆朝,事情就败坏得一塌糊涂,无可奈何了。
高士奇一解职,徐乾学势炎熏天,而其弟徐元文的地位更高一级。
小于成龙又做了总宪,在皇帝面前揭发高士奇、徐乾学的罪过,得罪了许多人,被大家群起而攻之。康熙帝对他也很不满意,“在宫门上骂”,问道: “他们几个同我读书的人,你必定都要弄了去,为什么呢?”小于成龙笨笨地回答: “臣为什么?不过是为尽忠报国。”
此处,小于成龙可谓是“事君以道”,尽为臣子的义务。而康熙帝则是以“能群”的方式优待帝师们。《荀子·君道篇》说: “君者何也?曰: 能群也。”也就是,能容人,能爱人,“泛爱众”的意思。康熙帝尽量保全大臣,不求全责备。与历史上某些皇帝如朱元璋之无情的大清洗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康熙帝也并不是一味纵容大臣招权纳贿,而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解决。往往是因为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的时候,就拿贪污受贿说事儿,整肃大臣。
有一天,康熙帝又与高士奇谈起有人说他招权纳贿的话。高士奇问: “是谁说的?”康熙帝说: “就是你平时所夸之熊赐履也。”高士奇说: “即此可见,臣在皇上面前说人不好,非与臣不好,说人好,非与臣好。但是别人说臣还可,熊赐履说不得臣。臣虽不与之相交,而书札时常往还。他与臣书,说臣人品是程朱一流人,岂有程朱会招权纳贿的?”康熙帝说: “书札何在?”
次日,高士奇取书呈上,康熙帝笑而存之。小于成龙常向康熙帝说高士奇的不是,而说熊赐履的好。康熙帝对他说: “你常说高士奇是小人,熊赐履是正人。看看这些信吧。”于成龙看完信之后说: “这就不晓得他们蛮子的事了。”于成龙是汉军旗人,无论满汉旗人都称南方汉人为蛮子。
不久,徐乾学因牵涉张汧案被解任,留京修书,而其弟大学士徐元文仍受到康熙帝的重视。他们虽被解职,但仍在南书房修书,还是在皇帝身边做事,只要是在皇帝身边就有招权纳贿的资本,依然我行我素。高士奇又指使左都御史许三礼上奏疏参劾徐乾学,康熙帝认为这些都是汉臣之间的嫉妒陷害,勾心斗角。康熙帝非常厌恶,说: “汉人倾轧,阴险可恶已极。”
许三礼参徐乾学的疏稿先让学生许时菴看过,徐乾学知道了,责备许时菴说: “许三礼有疏,与你同谋?”许时菴说: “此言何来?门生岂敢做此反复事?”徐乾学问: “你昨晚至其家,以疏稿相示,你若不同谋,何以不告我?”许时菴说: “看稿是有的,若以告,却不敢,因为两处皆是老师。此事门生原不与闻,偶然撞着,老师持以相示,敢不观看?观而遽以转告,倘老师先下手,中以祸,则门生将置身何地?如老师弹劾许师,门生断不敢与谋,若以稿相示,门生亦但观之,而不敢转告许师也。为门生者,职分如是足矣。”徐乾学仰天叹息: “人之不同也如此,当日成荣若不过一年友,每次见面必唏嘘相戒说,‘家君(父)未尝一刻忘年兄,年兄其备之。’父子不顾,尚披露肝胆如此,而年兄遂忍不以告?”
许时菴说: “老师若引此,门生知罪矣。门生诚然不能效此等肝胆也。”
康熙帝非常反感大臣之间的相互攻讦,曾借故责问于成龙为什么不能像徐乾学那样做文章。康熙帝之所以容忍徐乾学,在于他拟的圣谕总是能够称旨,与皇帝的心思符合。并非康熙帝不知道他的劣迹。康熙帝又想处置许三礼。许三礼闻到风声,情急之下,更把徐乾学的大罪状胪列出来复参一本。徐乾学就被攻倒了。康熙帝为人宽厚,不忍心将这些帝师置于死地“立正典刑”,只是罢了他们的官,让他们回家养老。为了给他们面子,并不押送回籍,而是要他们主动辞职。徐乾学还恋恋不肯辞,康熙帝对高潢说: “徐乾学是你的同年,何不劝之去?”
高潢就把皇帝的意思转告了徐乾学,而徐乾学竟然不信。高潢说: “皇帝的旨意我敢伪造吗?何况年兄在此,可以照应我们,怎么能希望你走呢?”
徐乾学只好上本请辞,康熙帝立即允许他辞归。徐乾学又固请陛辞,见到皇帝,喋喋不休,康熙帝很不耐烦,但仍然忍着。徐乾学说: “臣一去,必为小人所害。”康熙帝问: “小人为谁?”徐乾学说: “满汉俱有。”康熙帝问: “你们汉人相倾相害,满洲谁害你们?”徐乾学又说: “但要皇上分得君子小人,臣便可保无事。”康熙帝问: “如何分?”徐乾学说: “但凡说臣好的便是君子,但凡说臣不好的便是小人。”康熙帝强忍住怒气说: “我知道了,你去吧。”
徐乾学在老家江苏昆山受到两江总督傅拉塔(明珠的外甥)的监视。傅拉塔弹劾徐乾学及其弟徐元文的家人、门客诸不法事,徐元文遂解任,“惊悸呕血而死”。明珠复职以后,常有告讦徐氏者,徐乾学日日处在惊惧之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有诏取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三人回京修书。而徐乾学本来是希望皇上有朝一日还会起用他,但是近来风声特紧,他只知有使者前来,而不知其来召之意,疑有不测之祸,做贼心虚,竟然以惊悸死,也许是心肌梗塞。理学家处在危难之中,就不会如此。徐乾学、徐元文兄弟的学问修养都不好,徐乾学平时文字敏捷,文章常能称旨,然而没有修身功夫,一到临危之际就现原形了。
康熙帝理学修养深厚,为人慈爱,对大臣非常客气,比雍正帝、乾隆帝要宽宏大量得多。尤其是对于帝师们,遣回老家就是最重的惩罚了。李光地称之为“如天大度”。他所以骂小于成龙,是因为他知道,无论是京官或地方官都普遍贪污受贿,都罢了官,国家机器就要停止运转了。然而既然国家机器要运转,皇帝就不能制止御史们弹劾贪官污吏。其实,弹劾权也是大臣与皇帝分权的一种方式,尽管这仅是很有限的分权。就这一点来说,康熙朝君臣分权的情况比较正常,国家机器的程序化程度比较高,雍正帝则破坏了国家机器的程序化,到了乾隆帝时,大臣就不敢丝毫违背皇帝的意志了。
康熙帝除了反感汉臣们的相互倾轧,贪污受贿的卑劣行径以外,他甚至还认为所谓理学名臣们大都是名不副实的。康熙帝看到理学家们往往言行脱节,引起他对理学真伪问题的重视。他对侍讲官张玉书等人说: “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然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他一再批评汉官说: “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不过,康熙帝并不因理学家的言行不一而否定理学本身的积极意义,这种从容客观的态度,比起某些人的激进态度,高明多了。康熙帝颇不赞成当时一些理学家夸夸其谈的作风,他曾说: “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如熊赐履攻击李光地“不识一字,皆剽窃他人议论”。而李光地则说熊赐履“不讲学问,但以明末门户人语说过”。李光地说: “我初入翰林时,孝感(熊赐履)声望甚重,就是嚼签子事,天下都不信,还说是索(额图)公害他,没有这事。假使孝感不落东海(徐乾学)圈套,竟不复出,其声名到后代了不得,却被这再次起用弄丑了。”
至于李光地,康熙帝也曾有微词,说: “朕一生所赖者,惟在记性……前李光地所作一本《易经》讲书,朕留在内。顷者《周易折中》告成,因复发出。李光地以为奇异,奏曰‘此有何紧要之书,乃臣幼年所作,全无足取,上犹记忆发出’。”又左都御史徐元梦奏谓: “前年李光地过浙江,语臣曰: ‘我自幼年留心易学,数年修《周易折中》,常听皇上教诲,较前觉有可信。’”康熙帝认为,李光地前后所言,判若二人。这本来没有什么,皇帝却要较真。李光地曾说: “欲人主辨奸,难矣哉!”
明珠、徐乾学又曾举出翰林院侍读学士德格勒假借道学之号以欺世盗名,他因为学问不精,而受到整肃。而德格勒为李光地荐举,徐乾学意在倾轧李光地。
康熙帝问李光地谁精通《易经》?李光地就推荐德格勒好读书。康熙帝用德格勒讲《周易》,问他的《易》学,是何人所传授,德格勒说是从李光地学的。康熙帝问,你尽得李某所学吗?德格勒说: 尚无百分之一。康熙帝又问,李某尚有他学否?德格勒说: 《性理》各经俱精通。
但是徐乾学一再要德格勒向皇帝进言,除去奸臣明珠,终于惹怒了皇帝。有一次,天大旱,皇帝让德格勒揲蓍占卦,得夬卦。
德格勒说: “泽在天上,有雨,但决去小人,便立降甘霖。”康熙帝问: “小人在何处?”德格勒答: “阴乘阳,逼近九五,乃得时得位者。”把矛头指向宰相。康熙帝问: “如何去之?”德格勒答: “卦辞说‘扬于王庭’,自然明正典刑。”康熙帝说: “以我的看法,彖曰‘健而说(悦),决而和’,‘和’‘而说(悦)’,似不动声色,而隐然去之,岂不更好?”德格勒说: “‘健’与‘决’,似终从斩截为好。”
德格勒借讲《易》之机,有意曲解《易经》,诳皇帝除去明珠,如果遇上不学无术的皇帝,这一套也许可行,偏偏康熙帝学问高深得很,看出德格勒心术不正。如果德格勒像小于成龙一样揭发明珠的劣迹,皇帝对他还要尊敬几分,现在则弄巧成拙。
德格勒立即受到整肃,下狱受审。徐乾学命大司寇追究德格勒受何人指使?意在倾陷李光地。德格勒受夹刑,始终不攀扯李光地。
德格勒对主审官图讷说: “君为法司,而用刑不严,我不痛,安得成招?”图讷问: “如何是严刑?”德格勒说: “夹我的足我有何痛?一夹就睡过去了,舒服得很。如果把夹棍往我头上夹,我就害怕了。”
图讷知道德格勒想以死殉志。而事前皇帝有旨: 糜烂其皮肉无不可,但须留一活口。图讷不敢夹德格勒的头,据实复旨。康熙帝为什么不许杀德格勒?因为他令班弟去抄德格勒的家之后,发现德格勒穷得很,他毕竟是清官,不能不予以保全。
班弟回奏: “其母亦恨德格勒之狂妄。但其家实无一物,敝衣粝食,穷苦不堪。”康熙帝问: “他难道把财物转移了?”班弟答: “不太像。”
后来李光地也被诬陷,遭弹劾,受审查。德格勒是李光地推荐,自然要追究李光地的欺君之罪,李光地回答: “我只荐他有志肯读书,并不保其为人。但不曾奏明其狂妄,则认罪。”主审官据此复旨。移时,宣布圣旨: “李某从来奏事不欺,如平台湾,举朝无有建议者,而李某主其议。只有荐德格勒一节错,今既已服罪,令他还到掌院任职。”
李光地受审之日,恰逢日食。“问口供时,日食将既,人面才见影,天昏地暗。及旨意出,日方复圆。有以此为言者。”李光地说: “天变乃一定之规,与此有何关涉?”其人说: “恰巧遇此,便是天意。”李光地懂得天文,并不以日食现象为灾难祸福的征兆。但是巧合的事情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李光地受人倾轧,遭到皇帝猜疑,明察暗访,常常处于危惧之中,然终能化险为夷。康熙帝说: “李光地久任讲幄,简任纶扉,谨慎清勤,始终如一。且学问渊博,研究经籍,讲求象数,虚心请益。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有过于李光地者”。
李光地谨小慎微,清廉自立,不卖官受贿,也就遭人忌恨。有一年,李光地入京,在维扬遇到吴玉老先生。吴先生对他说: “你作编修,可谓荣遇,此行,我觇你的气运,可卜远大,然而英气亦害事,士无论贤与不肖,入朝见忌,不可不慎。”
李光地问,如何避免英气害事?吴先生说: “不可与皇上私语,对奏须在人共见共闻时,若是单独对奏,讲话须高声。”这两句话,李光地终生守之。在他晚年,皇帝多次就立太子之事单独与之密谈,不过,此时他的地位巩固,已经没有危险了。
临别时,吴先生又说: “内有中书高士奇者,此时官虽小,然非久居人下者,君须留意。”后来一一如其言。
李光地乡试中举时,吴老先生做主考官,吴先生遍观诸人,独指李光地说: “李兄第一远大,其精神足,皆内敛。”对众同年说: “你们都要学此。”又特指李光地的表弟吴某说: “君尤当学李年兄。”并问吴某年岁、家世、父母、子息,吴某说,尚无子嗣。吴先生愀然说: “父母之身,须当保重。亟学李年兄。”
吴某甚恐惧,丁未年会试不中,回家时又在淮河舟中遇吴先生,还是如此说。庚戌年,他们兄弟共同登进士第,表弟吴某即死于北京。吴先生之神鉴如此。
可见人要免除命里注定的灾难,只有做好人行好事一途,别无他法。李光地能免于灾难,并非如某些学人所说,是善于玩弄权术。如果道德修养无济于事,只有权术可以保身,明珠、徐乾学一类大臣为什么也会倒霉?现代某些学人不知为什么对于古人的道德修养就是要一笔抹杀为快。
康熙帝对于汉臣互相倾轧十分不满,说: “许三礼参徐乾学荐举熊赐履,往者皆言熊赐履不好,今见朕起用熊,又言熊赐履好……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甚佳,汤斌又谓不然。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
熊赐履去世之后,康熙帝对其评论说: “朕尝潜玩《性理》诸书,若以理学自任,则必至于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反之于心,能实无愧于屋漏乎?宋明季之人,好讲理学。有流入于刑名者,有流入于佛老者。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殁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有人指责熊赐履的理学功夫不行,康熙帝也有同感。至少他嚼签字一事,反映了他道德有亏。
大学士王熙说: “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若各立门户,各持意见,互相陷害结仇,何云道学?”而康熙帝认为: “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康熙帝主张讲学不应各立门户,但如果确有真知灼见,又能坚持一己之说,也是完全许可和值得提倡的。其实,变易其说也是正常的,即使自相矛盾也不妨,关键是要有求真的态度,而不可以固持一边,对于程朱与陆王,不必抱定一边,排斥另一边,两边相互融合才能透彻明理。
理学家常常以语录的形式发表思想,有些人可以借此掩盖自己的文采不足。康熙帝认为,文章如果写得不好,就是假理学。他说: “从来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文之士必须能明理,而学道之人亦贵能文章。朕观周程张朱诸子之书,虽主于明道,不尚词华,而其著作体裁简要,析理精深,何尝不文质灿然,令人神解意释。至近世则空疏不学之人,借理学以文饰其陋”。这种认识基本上是对的。因为人的思想是由语言组成的,文字反映了人的思维状态。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今人多不能懂,首先就是因为语言不通。但是,这也是一边之理,另一边的道理也要知道,即文章与道德也可以毫不相干。
康熙二十一年,吏部题补内阁学士员缺时,开列名单内有崔蔚林其人,康熙帝读了他的文章,说他无知,“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并说: “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帝先读了他的文章,又考察其实践。这种思路也是对的。关键是考察是否客观。许多所谓考察往往是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
康熙帝对于张伯行也不完全满意,曾批评他: “朕昨召进张伯行,令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处,彼全不能讲……张伯行自谓知性理之书,性理中之《西铭》(张载)篇尚不能背诵,以为知性理,可乎?凡人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张伯行为巡抚时,有人逢迎,彼即喜之”。张伯行不能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能正是他明理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的这句话长期以来都被人们理解为,老百姓只能受驱使(使由之),不能让他们明白道理(使知之)。由此认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张伯行大概是不同意这种解释的,然而又不能给出更合理的解释,所以就“全不能讲”了。中国文化因为遭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难,出现了断层,后人对于古人文字的解释,不太可能完全准确,孔子的这句话一直被误解。直到前些年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孔子的话才有了正确解释的依据。孔子这话的意思是,只能以身作则带领老百姓去做(使由之),不能教导老百姓应该去做什么(使知之)。可惜张伯行没有看到郭店楚简。至于说张伯行不能背诵张载的《西铭》篇,就断定他是不懂理学,就是把理学当成记诵之学,更没有道理了。由此可见,康熙帝自己并非真理学家,顶多算半个理学家。
清初的理学名家,有数十人,依康熙上述所品评把理学名臣都视为假道学,而能成为名实相符的真道学者,恐怕只有康熙帝自己了。
清初盛世的出现,与理学名臣对于国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他们很难做到言行一致,某些人如徐乾学为了个人的名利,败坏了社会风气。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道理不明,他们常做主考官,把一些道理不通的卷子认做好文章,选拔出的科举士人就不能治国。李光地的意见是很正确的,即使没有科场舞弊,学术有偏颇,国家也要遭殃。
明末,中国学术败坏,士风日下,导致人心涣散,出现了上下交争利的腐败局面。清初学者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王学末流的泛滥。如黄宗羲说: “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世贞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顾炎武认为王世贞“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陆陇其说: “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至于天启、崇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古人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在读书人的肩上,认为他们的学问道德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也讲得通。
其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程朱“言行一致”并无不同。王学末流固然不足道,然而程朱后学也未必可观。有鉴于此,康熙帝对于当时的理学名臣十分求全责备。康熙帝认为读书明理,贵在学以致用。所谓“道学之士,必务躬行心得”。道学即是理学,又称新儒学,有别于孔孟之旧儒学。康熙帝认为假理学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认为汉人道学家大多如此。
对于那些平日以理学自居而言行不一的帝师们,康熙帝虽未公然斥之为假理学,但也不以真理学视之。这些人都遭到或轻或重的整肃。
康熙二十一年,吏部题补内阁学士员缺时,开列名单内有崔蔚林其人,康熙帝读了他的文章,说他无知,“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并说: “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帝先读了他的文章,又考察其实践。这种思路也是对的。关键是考察是否客观。许多所谓考察往往是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
康熙帝对于张伯行也不完全满意,曾批评他: “朕昨召进张伯行,令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处,彼全不能讲……张伯行自谓知性理之书,性理中之《西铭》(张载)篇尚不能背诵,以为知性理,可乎?凡人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张伯行为巡抚时,有人逢迎,彼即喜之”。张伯行不能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能正是他明理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的这句话长期以来都被人们理解为,老百姓只能受驱使(使由之),不能让他们明白道理(使知之)。由此认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张伯行大概是不同意这种解释的,然而又不能给出更合理的解释,所以就“全不能讲”了。中国文化因为遭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难,出现了断层,后人对于古人文字的解释,不太可能完全准确,孔子的这句话一直被误解。直到前些年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孔子的话才有了正确解释的依据。孔子这话的意思是,只能以身作则带领老百姓去做(使由之),不能教导老百姓应该去做什么(使知之)。可惜张伯行没有看到郭店楚简。至于说张伯行不能背诵张载的《西铭》篇,就断定他是不懂理学,就是把理学当成记诵之学,更没有道理了。由此可见,康熙帝自己并非真理学家,顶多算半个理学家。
清初的理学名家,有数十人,依康熙上述所品评把理学名臣都视为假道学,而能成为名实相符的真道学者,恐怕只有康熙帝自己了。
清初盛世的出现,与理学名臣对于国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他们很难做到言行一致,某些人如徐乾学为了个人的名利,败坏了社会风气。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道理不明,他们常做主考官,把一些道理不通的卷子认做好文章,选拔出的科举士人就不能治国。李光地的意见是很正确的,即使没有科场舞弊,学术有偏颇,国家也要遭殃。
明末,中国学术败坏,士风日下,导致人心涣散,出现了上下交争利的腐败局面。清初学者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王学末流的泛滥。如黄宗羲说: “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世贞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顾炎武认为王世贞“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陆陇其说: “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至于天启、崇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古人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在读书人的肩上,认为他们的学问道德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也讲得通。
其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程朱“言行一致”并无不同。王学末流固然不足道,然而程朱后学也未必可观。有鉴于此,康熙帝对于当时的理学名臣十分求全责备。康熙帝认为读书明理,贵在学以致用。所谓“道学之士,必务躬行心得”。道学即是理学,又称新儒学,有别于孔孟之旧儒学。康熙帝认为假理学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认为汉人道学家大多如此。
对于那些平日以理学自居而言行不一的帝师们,康熙帝虽未公然斥之为假理学,但也不以真理学视之。这些人都遭到或轻或重的整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