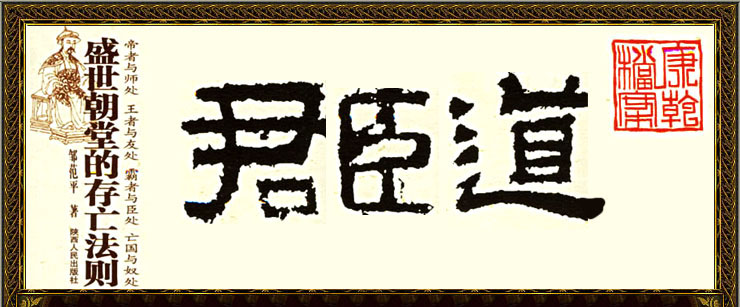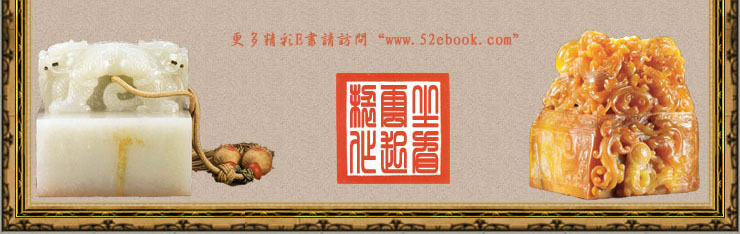在雍正帝的寝宫,养心殿西暖阁有一副他手写的对联“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充分表达了他独揽朝纲,集天下庶务归于一身的愿望。这副对联的上联反映了雍正帝的工作作风非常严刻,甚至容不得臣工有违背他的念头。
唐代以来,深居在宫墙之内的皇帝,依靠着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统治中国这个广大的帝国。这个官僚机构的最高一级中枢机构是中书省,中书省的首长是宰相。然而,一切事务都委托宰相办理,皇帝不能放心。人主要是通过眼睛看的功能了解外界,除了直接观察事物以外,就是看间接的文字媒介。皇帝了解下情主要的管道就是看臣下的报告。历朝历代的文书不尽相同,有章、奏、表、议、疏、启、记、札子、封事等诸多名目。明清奏章文书有奏本和题本两种形式。凡有关政务、军事、钱粮、刑名、弹劾等公事,皆用题本,由官员用印具题;凡有关个人的事务如到任、升迁、告假等私事则用奏本,不得用印。此外,还有京官所用的部本和地方官所用的通本(都含有题本和奏本)。奏章先送通政司转交内阁入奏,既不易保密,速度也很慢。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宰相擅权,干脆取消宰相。皇帝与外界联系,了解下情的手段是批阅臣工的奏章。朱元璋每天要看的奏章太多,忙不过来,于是要求上奏的官员写出奏章题要,用黄纸贴在奏章文书的末尾,以便于皇帝阅读,称为“贴黄”。但是,皇帝光读内容提要之贴黄也还是忙不过来。朱元璋乃设大学士数名代替宰相做顾问,以内阁代替中书省。奏章经通政司转内阁,由大学士先阅读,然后在每一份奏章中夹上小纸条,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建议,送皇帝裁定,这就是所谓“票拟”。
朱元璋不信任内外臣工,也不信任太监,他之后的明朝皇帝则不然,以为太监是最可爱的人,专门任用太监做监督。皇帝为了镇压官员中的反对派而先后建立了特务机关——锦衣卫和东、西厂,广布耳目,密探遍于国中。太监系统的特务机关,除了给民间制造白色恐怖以外,皇帝根本不能依靠他们了解外界的情况,只能造成太监窃取皇权的局面。明朝中后期,票拟由太监送达皇帝,并由太监在皇帝面前作解释,皇帝的旨意又是由秉笔太监来完成,或口头传达,即所谓“口含天宪”。明朝在太监刘瑾、魏忠贤等人专权时,言路不能畅通,皇帝的权力被太监窃取。
清朝统治者接受这个教训,严禁太监干政,也不再设立特务机构,主要是通过密折制度来了解下情。清朝沿用了明朝的票拟制度,但在具体做法上防止了明朝的弊病。明朝的奏章,只有奏本和题本,没有奏折。奏本和题本手续繁复,经过通政司和内阁,再送达御前,收复迟缓,容易造成泄密和壅蔽现象。
人们往往把“奏章”与“奏折”视为同一物的不同名称,这是误会。“奏折”一词始见于顺治朝,奏折也称奏帖。“折”即折叠之意,用折叠的纸缮写,可以舒展叠合,十分方便。清末,废题本,专用奏折。“密折”一词则始用于康熙朝。康熙帝曾经说: “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前朝皆用左右近侍,四外探听,此辈专好颠倒是非,肆意妄行,援举奸佞,偾事甚多。”奏折是一种机密文书,可以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拆看,简便迅速而且保密性强,它是康熙帝加强皇权的一种有效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这种手段有利于皇帝了解情况,不易为左右所蒙蔽。 密折制度当然比特务制度高明许多。明朝的东、西厂直属于太监,锦衣卫随意捕人,权力极大。清朝官员仅仅是传递情报信息,裁决之权仍在于皇帝手中。
康熙朝,专为皇家在江南采办物资的皇帝家臣,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就兼有为皇帝秘密搜集情报的职责。有一次,康熙帝在李煦的奏折上批示道: “朕体安,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
康熙帝在曹寅的奏折批示道: “朕体安善,尔不必来,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非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康熙帝曾批示户部尚书王鸿绪奏折: “京中有可闻之事,卿书奏折与请安折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但有泄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王鸿绪在奏折中写道: “臣此密折,伏祈即赐御批密发,并望特谕总管面交臣手,以免旁人开看之患。又折子封套之外,用纸加封,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以隐臣名,合并声明。”
奏折最初为一种特权,仅限于少数内务府包衣、旗下家奴和亲信官员使用,他们与皇帝之间可以直接联系,他们的职务较低,便于监视地方官员的行动。地方大员如巡抚的奏折之权,是在以后。巡抚的奏报只能循例以题本或奏本的形式上达,以后才获准上奏折。若有上奏之事,可经过有权上奏折的官员代传,如江苏巡抚宋荦、张伯行的奏折就是由李煦代为呈进的。
地方和中央大员普遍获得奏折权,是在康熙五十一年前后。凡涉及机密事件,不便露章上奏者,皆可以亲自写具奏折上达。康熙帝还特别强调,官员一定要亲自书写奏折,词但达意,不计较字画工拙。有的武官不能亲自书写,可由亲近子侄代写,但必须在折尾加以注明,这些都是为了保密。
雍正帝继位以后,为了熟悉和掌握国家的各项事务,确知各种实情,将密折制度进一步扩大化和强化,他下令各省督抚密上奏折,“凡督抚大吏,任封疆之寄,其所陈奏,皆有关国计民生,故于本章之外,准用奏折。以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使得封疆大吏们普遍有了这一权力。
当然,要真正了解实情,必须是这些官僚能够汇报实情。怎样使官吏们都汇报实情呢?雍正帝的办法就是扩大上密折官员的人数。不久,他又将奏折这一权力进一步扩大,雍正元年(1724年)二月,雍正帝在给科道官员的上谕中说: “朕仰承大统,一切遵守成宪,尤以求言为急,在京满汉大臣,外省督、抚、提、镇仍令折奏外,尔等科道诸臣,原为朝廷耳目之官,凡有所见,自应竭诚入告,绝去避嫌顾忌之私,乃为尽忠。今着尔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时务,皆许具实敷陈。其所言果是,朕即施行,即或不甚切当,朕亦留中不发,不令人知。倘有徇私挟仇等情,巧为渎奏,亦不能惑朕之耳目,折内之言不许与人参酌,如有泄漏或同僚知而言之,则同僚即可据以密闻,朕将两人之折合验,事情必不能隐讳推诿。”
皇帝要能够及时确知各处的实情,得到低级官吏的直接报告是很必要的。于是雍正帝又给予道员、知府、同知、副将一级的官员密上奏折的权力。据统计,当时上奏折的人数达到1000人以上。
这样做有明显的好处: 官员密折上奏,而且上奏的人很多,使得事情不好隐瞒,也不敢隐瞒。某件事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别人奏了,自己不奏,就是渎职。上奏之权没有人可以垄断,歪曲事实的奏报可能被其他真实的奏报揭露,所以普遍密奏也有利于皇帝了解事实真相。有一次,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报,广东龙门营千总刘贵,在巡查中遇到匪徒,追捕时被杀身死,匪徒业已抓获,题请正法,并请治疏忽之罪。雍正帝批道: “地方上凡遇此等事件,但要据实奏闻,何罪之有?若隐讳支饰,则反获罪于朕矣!”
扩大密折网,是雍正帝加强集权的方式,使得下对上也可以形成某种权力,这种权力不是传统方式,如臣下对皇帝的“封驳权”,而是下官对上级或官员之间的监督权,并且监督权是通过皇权来体现的。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监督权是皇帝给予的,他们往往是奉旨监督,奉旨打小报告。在封建时代,下级不可能公开地监督上级,密折方式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雍正帝以密折制度令文武互查,上下级互查,使以往只有上级监督下级的状况有所改观。下级属员向皇帝汇报主官的政绩,以便于皇帝了解臣工,听取多人的意见。这在封建社会也是一项有积极意义的改革。
官员们必须相互监督。为了加强对督抚大员的监督,雍正帝鼓励布政使以下的官员直接向他上奏折。他批示福建布政使黄叔琬的奏折说: “你等两司之职,向来不能直接上奏,现在特许你等密折奏达,但切勿借此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礼。若遇督抚有不合宜处,只可密行奏闻,不可向一人声扬。你但勉力秉公,实心效力,朕自能洞见也。”雍正帝一向非常自信,以为可以洞察一切。以前是上级监督下级,现在下级也可以监督上级,使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也稍知畏惧,不是畏惧下级本人,而是畏惧下级密奏。
密奏的主要内容是筹商、官吏考评、地方吏民动向等等。雍正帝的重大改革往往都是经过密折奏批,君臣反复密商而后决策的。凡是官员认为可奏之事,无不可以上奏。雍正帝对地方官员提出这一要求,他给陕西宁夏道鄂昌的批示说: “今许你等下僚亦得奏折者,不过欲广耳目之意。于你责任外,一切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饬,雨晴是否得时,百姓之生计若何,风俗之淳朴浇薄怎样。即使是邻境远省,以及都门内外,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真知灼见,都可以风闻入告也。”密奏,已成为官员们的责任和义务,也不论分内分外之事。
凡臣下奏折所提之事不便处理,即将奏折留在宫中,称之为“留中”。
奏折既可以陈事,也可以论人或荐举人才。雍正帝曾下旨: “内而大臣以及闲曹,外而督抚以及知县,有适当人选,便可具折密奏。”两年后,荐举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京官自翰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道员、学政以上,武官自副将以上,旗员自参领以上,皆令各举一人。”
雍正帝考察“模范督抚”李卫,就是典型的奉旨密告。
李卫初任云南盐驿道时,雍正帝让云南永北镇总兵马会伯,查访李卫的行为。他在马会伯的奏折上批道: “近闻李卫行事狂纵,操守亦不如前,果然否?尔一毫不可瞻顾情面,及存酬恩报怨之心,须据实奏闻。”
马会伯据实回报: “李卫虽赋性急躁,貌似狂纵,却并非乖张悖谬,操守依旧如初。”
李卫任云南布政使时,与贵州威宁总兵石礼哈互相攻讦。二人并不曾共事,一在云南,一在贵州,石礼哈折奏李卫,只为事机不密,被李卫得知,从此誓不两立。雍正帝又把他们二人的奏折发给云贵总督高其倬评判。高其倬认为,两人各有其优缺点。贵州大定总兵丁世杰,折奏李、石的人品官箴,认为他们二人气量狭窄,有负皇恩,而总督高其倬、巡抚毛文铨有徇情之弊。雍正帝将李卫调离云南,升为浙江巡抚。
后来雍正帝又将李卫与石礼哈互参的奏折发给鄂尔泰,令其评判。鄂尔泰回奏: “臣查石礼哈多躁进之心,无坚定之识,然努力办公,殊可以济事。李卫曾面告臣,此去云南,须防备石礼哈。臣云: ‘人但自防,何用防人?’(雍正帝批道: ‘此朕生平之夙志,从来之居心。但知畏天,从不畏人。此朕时常训谕廷臣者’)李卫也首肯臣所言,只说: ‘你到那里去就知道了。’臣赴云贵,石礼哈与臣始终相安无事。李卫、石礼哈皆与臣和好,极相敬重。然论心地,李卫颇正,石礼哈近于狡黠;论人品,李卫高尚,石礼哈卑劣。”雍正帝可能是受了鄂尔泰的影响,对李卫的缺点不予严厉追究,对石礼哈则屡加责备。
李卫任浙江巡抚时,雍正帝又命李卫查访新任黄岩镇总兵董一隆,在他的奏折上批道: “待其莅位后,细加察访,密奏以闻。”
大理寺卿性桂赴浙江清理仓储钱粮之时,雍正帝命他“凡有风闻之事,即行奏闻”。性桂折奏称: 杭州将军鄂弥达与李卫不睦。
河东总督田文镜奏称: “李卫操守廉洁,臣所素闻,听说其官俸偶有缺乏,则取之于家,绝不以权谋私,真乃当世之贤员,所谓难能可贵者也。但好戏游,图游冶之欢于一日,则千百行为受玷污矣。其驭吏绳尺,未免稍微宽疏,振肃规模,未免少于稽查,则于高官大僚之体有不合宜之处,于皇上任使之意亦有所辜负。”田文镜与李卫并不在一省共事,也可以监督和批评。来自多人奏折的评价,使皇帝对李卫的认识就比较接近于真实了。
又如,雍正帝命重庆总兵任国荣,留心查访四川文武官员的声名。任国荣回奏: “四川学政宋在诗,公正廉明,声名甚好;川东道陆赐书,办事细心;永宁道刘嵩龄,人明白;永宁协副将张英,声名平常;漳腊营游击张朝良,操守廉洁,谙练营武,但不识字”,等等。
李绂与朱纲当时深受雍正帝信任,但也须加以考察。雍正帝派李绂为广西巡抚的同时,又命原广西署抚、提督韩良辅“细访其吏治,密奏朕知”。
朱纲任湖南布政使,雍正帝在湖南巡抚王朝恩的奏折上批示: “朱纲行为举止,舆论褒贬不一,依朕观之,他似欲尽快有所成就,然否?据实奏来。密之!”反过来,雍正帝又命朱纲访查他的顶头上司王朝恩: “朕观其为人,于地方吏治颇为谙练,但才具微觉狭小,你可事事留意,看其居心行事,倘少有不妥处,即可密奏以闻。如稍加隐匿,不以实告,欺蔽之过,你难辞其咎也。”
王绍绪由鄂尔泰举荐而授广东提督,雍正帝以为王绍绪“明敏稳妥”但“偏于善柔”,未免有行小惠而沽名钓誉的毛病。他命广东将军石礼哈考察王绍绪,“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密奏说: “王绍绪居官行事稍涉琐细,然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雍正帝又询问两广总督孔毓珣: “王绍绪何如?克胜此任否?”另一方面又命广东巡抚傅泰进行调查。傅泰密折答复说: “王绍绪操守极好,为人稍觉柔懦。”傅泰受命监视奏报了提督王绍绪的情况,又受命监视奏报广东布政使王士俊、按察使楼俨的情况。他密折奏报王士俊“才具练达,办事勤敏,于藩司之职,颇称胜任。但观其举动言论间,似有自得自矜之意”。他密折奏报楼俨的情况: “于刑名非所谙”,“年已六旬以外,疾病缠绵,精力渐衰,诸事不能周到”。
傅泰同样也处在自己的监视对象王士俊的监视之下。雍正帝命王士俊反过来访察傅泰。他在王士俊的密折上朱批道: “傅泰识见甚不妥协,汝意以为何如?其操守若何?居心立志若何?办事才干若何?统率属员公私明暗若何?秉公抒诚据实奏闻。”王士俊就自己的观察印象密折回复说: “傅泰胸无定见,毫无可否。偶有议论,亦属平平”,“访闻粤海关新充书办陈炳文、范九锡、潘栋、高维新、柳大本五名,傅泰每名各得银三百两,方准入册。傅泰之操守,臣未敢信其廉洁也”。雍正帝认为王士俊所评“甚属公道”,严责傅泰,最后将其降调回京。雍正帝在傅泰的折子上批示:“用人且莫生疑,如有人欺我,听其欺之,无有不败露者。败露时不得轻易放过,如此则人人畏服矣。”(《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7册,51~57页)。
雍正帝通过两广总督郝玉麟对布政使王士俊又有所了解,郝玉麟描述王士俊说: “察其言论,推其居心,委属明达有本之人。”反过来,雍正帝也暗中指示王士俊监视郝玉麟: “观郝玉麟自到任以来,惟以清楚钱粮为要务,朕已批谕训诫矣。如有太过处,汝可尽力规谏之,不妨将朕此谕作汝意,微露令知之。”王士俊具折密报云: “广东督臣郝玉麟语言便捷,人似精明。到任后未能深悉土俗民情,将按察使楼俨起出私藏军器积恶窝盗之黄元捷提至肇庆,竟行保释……其近日施为,似非因地制宜除暴恤商之善政。”
雍正帝让臣工们相互监督显然是对他们不信任,或虽信任也必须进一步考察。确实,没有人是可以不疑而信的。不疑而信,根据何在?就做学问而言,古人也有“大疑大进,小疑小进,不疑不进”的说法。经过疑而达到信,才是正信和智信,而不是妄信和迷信。不疑而信,就是偏信。
雍正帝说: “待人不必信亦不必疑,过疑则失人,过信则自失。一事见信,不可即信其将来百事皆实,一事见疑,亦不可即疑其将来百事皆诈。”又说: “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所以可信者,乃是你自己取信;所以可疑者,乃是你自己取疑,赏罚也是如此,总与朕无关系。朕此一用人法,凡有统率之则者,都应该效法。”所以对人要既不疑,也不信,是因为“过于相信人,则不防其可能改变操守,而过于怀疑人,则可能不容其改正过失,均非时中之理”。
何谓“时中”?时中就是合乎时宜,无过犹不及之弊,《中庸》云: “君子而时中”。人做任何事情都可能会有两种对立的倾向,偏于一种倾向就是偏激。中庸的本意是平衡两端,恰到好处。可是现在人们误以为中庸即是不讲原则,似乎中国古人提倡不讲原则。中庸之道的智慧,人们确实不易掌握,而往往流于无原则的和平。在用人的问题上,雍正帝所遵循的中庸之道是不信不疑。他强调“必须时时加以访察,而后可以深悉”。
雍正帝通常的访察方式是,让某人的上下级官吏们暗中查访汇报,并加以评论,同时也要亲自当面考察,察言观色。他考察贵州布政使毛文铨时,先让当地官员上密折评论,得到的评价不好。他又亲自召见,面试之后大为欣赏,擢升毛为福建巡抚。可见他并不是专信汇报的皇帝。
雍正帝也依靠特务监视调查臣工。据传说,雍正帝在夺嫡时,于雍王府内招纳了一批三教九流,有的精通武艺,有的长于侦探,飞檐走壁,无所不能。他当了皇帝,就利用他们作爪牙。在内务府有一个所谓的“粘杆处”,粘杆处头目称“粘杆侍卫”,其余职员称“粘杆拜唐”,名义上是从事钓鱼、捕蝉、捉蜻蜓等闲散琐事,实际上是特务密探,办事的总机构设在雍和宫内。皇帝可以随时传旨到雍和宫,总机关得旨即拣派适当人员执行任务。分机关则设在皇宫御花园堆秀山前,山上的“御景亭”就是每夜值班瞭望的哨所,他们受雍正帝直接指挥。比如官员王某,身边有一仆人,在他离任返京前忽然辞职,并说,这些年你表现很好,没有违法的地方,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先回京去汇报。王某吓得出了一身凉汗。
这样,雍正帝就有了密折、面试和特务,三种考察方式,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雍正帝对自己信任的大臣也要怀疑,暗中察访,就避免了受骗。乾隆帝信任和珅不予考察,大臣们多次参劾和珅,乾隆帝也派人调查,就是查不出问题,以乾隆帝之精明怎么会被和珅蒙骗?如果乾隆帝也学雍正帝暗中察访,不会查不出和珅的问题。
雍正帝的宠臣田文镜曾说,常人只知道皇上操生杀予夺之大权而可畏,而不知皇上禀至圣至神之聪明而不可欺。雍正帝却认为,做君主甚难: 若对弊政不予改革,众人会说皇帝懈于政务;若竭力整顿,又会被人目为苛刻;对于言官的意见若不采纳,则是不能受谏;若以其言谬妄而加处分,则是堵塞言路。怎样做都难以令人满意,他因此制一玉玺曰: “为君难”。他从小就性情急躁,康熙帝曾以“戒急用忍”四字训诫之,他一直以此语警诫自己,并书写悬挂于居室之中。
最后,再把雍正帝与明太祖朱元璋作一番比较。表面上两人为政有相似之处,两人的作风都是严刻冷峻,雷厉风行。实际上朱元璋治国无方,雍正帝有章有法。朱元璋精力充沛,一天批阅一百多件奏章,裁决几百种案件。他决不相信大臣,只相信特务,依靠锦衣卫,搞恐怖统治,将特务政治制度化,使得明代政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政治。
雍正帝也是精力充沛,常常熬夜,一天批阅几百件奏折不在话下。虽然有时也依靠某些微官末弁监视臣下的行动,直接密奏,但绝不给予他们以特权。他所利用的监督手段,主要还是广泛的密折制度,虽不是下层舆论监督,但可称为上层舆论监督。当时有些官吏弹劾了别人,事后又解释说,我不参他,别人也要参他,皇上还要怪罪我。可见密折制度对官员们有很大的威慑作用。雍正帝是不许臣工们做老好人的,臣工有什么过失,很快就暴露出来。
明代中期,嘉靖皇帝信赖大奸臣严嵩,而严嵩劣迹斑斑,一再受到御史和其他官员们的弹劾,就是因为奏章不能直接上达,要经过一些中间环节,早被严嵩的耳目探知,提前作了准备,从容化解,而上疏者则遭受打击报复。严嵩独擅内阁二十余年,特务和言路系统都失灵,直到皇帝对他厌倦了,其罪行才“暴露”出来。
密折制度的好处是可使臣僚互相监督。但密奏往往不太可靠,隐恶扬善或诬陷他人或借密奏巧取功名者大有人在。康熙帝说: “密奏亦非易事,稍有忽略,即为所欺。”关键是对其认真鉴别和正确掌握。康熙帝要求臣下“若不可用露章者,应当密奏”(《康熙实录》卷二七五)。
雍正帝实行的密折制度与武则天的告密制度也不可相比,是比较理性化的。武则天对付臣子的手段可与朱元璋相媲美,朱元璋和武则天搞的特务机构,泛滥成灾。雍正帝搞特务监视也以“时中”为原则,适可而止,不使特务的权力膨胀过度。人们总是指责雍正帝严刻狠毒,其实,他为政往往很重视中庸之道。人们认为,以冷酷无情著称的雍正帝与中庸之道一点都不沾边,原因在于误解了中庸之道。单纯静态的中庸之道是不存在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必须有所偏重,向哪一边偏,须要视具体情形而定,治国如治病,关键在于达到阴阳平衡,阴盛则补阳,阳盛则补阴,在纠正废弛的吏治和普遍的腐败时,以猛治贪恰恰就是中庸之道。过了这一特定的时期,就有失中庸之道了。因此,密折制度不可避免会出现弊端。到了乾隆朝就有人要求废除密折制度了。事情总是反复无常,此一时彼一时,要寻出无弊端的言路,即使在民主社会也不可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