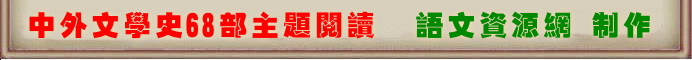|
教学要点:
人性、人道主义文学创作中的抒情性与精神深度的探索。
第一节 文学创作中人道主义思想的兴盛
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与兴盛。围绕人道主义展开的讨论与争议。小说形式的尝试与文学史意义。作品类型的多样性,精神探索的多义性。
第二节 苦难民间的情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张贤亮早期“反思”作品中对朴素的民间情义的歌颂。发掘普通人原始的内心美与人间温情,批判极左政治路线所造成的悲惨事实
诗人的气质,苦难的历程,坚实的理论素养直接影响了张贤亮小说风格的艺术构成,使他的小说既有现实主义的深厚,又有浪漫的色彩和哲理思辩的闪光。
(一)《灵与肉》《邢老汉和狗》写于早期,不矫情
(二)《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这是计划中的总称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九部系列中篇中最先写的两部。
总的情节: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章永璘,怎样经过了几十年的苦难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的故事。
《绿化树》写的章在1961年底到1962年初两个月中的事,作者选择了特殊而典型的时代环境--正是前两年“大跃进”的负效应显示其灾难性恶果的时期,涉及全国的大饥荒正严重威胁着每一个地区每个人。右派分子章从劳动农场释放到西北地区一个偏远落后的农场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故事从这儿展开,写了章与当地百姓之间的关系,他学习马列的过程及心灵的历变。
《绿》的成功:一是,现实主义的深入--深沉的反思气息,带有一种普遍意义和哲学意蕴;二是,不仅真切描写了特定历史下的严酷现实而且善于从中寻求美和诗意,带有浪漫主义风格。
大西北的风俗美和人情美,唤醒了章内心深层的对于美的记忆和追求,使他被扭曲、撕碎的心灵得到慰藉。马缨花,一个具有吉卜赛女人性格特征的善良美丽的荒原妇女,追求爱情的执着,对文化人的崇拜,对美好未来的信心,都体现了一种民族精神。作为反思小说,《绿》不是旨在揭示某个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而是通过一个知识分子在厄运的环境中其所见、所闻、所遇、所思、所行,展现那个特定时代和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和文化传统,真实反映了一个被剥夺做人的权利,完全失去自我的知识分子,怎样在人民群众的爱护哺育下,在对真理的追求中,一步步恢复自我、超越自我。在此基础上反思历史,主题具有多义性、广阔性和丰富性。《绿》侧重从物质角度--饮食、饥饿揭示人的生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侧重从精神--性、爱的情感展现人的本质,人性的扭曲、异化和还原。
章在极度痛苦而失落自我的时候,黄香久以女人特有的魅力和情感,换回他对灵与肉的渴望,生活中终于出现些许亮色,然而成婚之夜,他才发现自己丧失了男人的基本本能,黄香九以她真挚的爱使她再次复活,复活了本能,也同时复活了他的理性,他开始怀疑这种纯兽性的性爱,他们最终分手。一个除了低层次的本能之外(生命一半,女人)还有更高层次的理性的精神追求(生命体的另一半,事业、信念、理性),当黄以自己的爱塑造了章的半个世界后,她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而另一半世界--理性的追求信仰的重建和精神的超越,得以复活为人的章独自去完成了。它以哲理性的审美方式,实现了人类自身本质的高层次反思。
第三节 美好理想的憧憬:《哦,香雪》
铁凝早期作品中的纯朴人性的表现及抒情化色彩。
附:女性主义小说双璧--王安忆与铁凝比较
王安忆 铁凝
第一阶段
1《雨,沙沙沙》 1《哦,香雪》
2《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 2《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3《六九届初中生》 3《四季》
纯真少女的心灵折光,是作者主观抒发的阶段
第二阶段
1《本次列车终点》 1《村路带我回家》
2《流逝》 2《老丑爷》
3《归去来兮》 3《醉年》
回归主题与人生况味的客观展示阶段
第三阶段
1《小鲍庄》 1《埋人》
2《大刘庄》 2《闰七月》
3《一千零一弄》
4《小城之恋》 3《麦秸垛》
5《荒山之恋》 4《棉花垛》
6《锦绣谷之恋》 5《青草垛》
7《岗上的世纪》
文化寻根与文化反思阶段
“三恋”“三垛”--女性身份的文化反省:
1、写作背景
1986年夏末,王安忆发表“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秀谷之恋》,无独有偶,与王安忆实力相当的铁凝,在这一年的深秋,则以北方式的冷隽,渐次推出了沉甸甸的“三垛”--《麦秸垛》、《棉花垛》和直到90年代中期才最后堆成的《青草垛》。虽然,从内容到形式,“三恋”与“三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或呼应,但巧合之中是否蕴含了某种相通的创作契机?80年代中期勃兴的文化与文化寻根热,曾使一个时期的作家、评论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自己的叙事立场和批评观点移入“文化坐标”中,试图通过个人的探索轨迹确立新的审美方向和价值体系。这一“文化坐标”轴纵向代表的是民族文化传统及文化心理积淀,而横向参照的是整体人类文化发展中的现代西方文化。无论自觉与否,寻根派与非寻根派的作家、评论家都在迫切地寻找与现代世界文学对话的“媒介”和“渠道”。对于中国作家而言,没有显著深刻的文化烙印,就等于没有走进世界文化视野的徽章,也就不可能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站在人类发展的共同高度审视人的存在,表现现代意识中的人类情绪。因此,焦躁的一代文人在强大的主流话语制约下开始了反叛和突围。由此可以断定,“三恋”“三垛”便是这种反叛意识和突围精神的实践。从文化的角度和意义上看,更是代表了那个时代作家的自觉选择,也不乏潜在的赶潮心态。
2、创作倾向
人类应该怎样理解人类、发展人类?应该怎样组成、维护一个相对稳定、合理的社会关系并向着更高的社会境界努力?这是全世界具有良知的作家们共同关注、执着思考的永恒主题。傅雷在30年代译介了法国作家莫罗阿的著作《人生的五大问题》,莫罗阿这样阐释了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本质:“在如此悠久的历史中,人类之能建造如此广大如此复杂的社会,只靠了和生存本能同等强烈的两种本能,即性的本能与母性的本能。必须一个社会是由小集团组成的,利他主义方易见诸实现,因为在此,利他主义是在欲愿或母性的机会上流露出来的。” [1]在莫罗阿的推论中,人类的基本关系是两性关系,而两性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即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则依赖于母性中的利他主义,那就意味着母性无私的爱、宽容、牺牲和奉献。这其中是否包含了男权思想呢?然而,早在20年代,茅盾译介的《爱伦凯的母性论》又让我们颇为惊讶地了解到,瑞典妇女问题专家(也被看作早期女权理论家)爱伦凯竟然也是极端地推崇着母性:“母性具有广大无边的力,他的本性,是'授予',是'牺牲',是'抚益',是'温柔',......利他主义的根即伏在母性内。”[2]而且,具有了利他主义根基的母性,能够消融利己与利他的冲突,消融精神与肉体的冲突,从而就能消融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矛盾和冲突。可见,无论是男权思想,还是女权意识,都不能够否认或回避两性关系之于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意义,也都不能够否认或遮蔽母性的力量和光辉。因此,性与母性是观照、探究人性、人的价值和命运的最直接的窗口。所以,尽管王安忆和铁凝并未有约在先,但灵感的指引,使她们的审美目光不期而遇,共同发现了一个让她们震惊、激动却又痛苦的“生命场”。
3、关于“性”
对于“三恋”和“三垛”中大量充斥着的性描写,曾招来尖锐的批评。如果按照一惯指导我们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认识论”去审视这些性描写,必然就会因为这些性描写孤立于社会环境、现实关系和道德力量而指责作品的失真或缺乏典型意义。甚至断定如此的性文学不能够进入审美层次。这也不奇怪,在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里,性一向被视为淫秽和丑陋之物而不登大雅之堂。所以,性与美无缘,与人生意义更是毫不相关。在历代文学作品中,性描写只是世风败坏、道德沦丧的写照。于是在大量的文本中,我们一方面看到荒淫无度的、放荡丑恶的性关系展示和渲染,一方面又看到板起的道德面孔在告诫警示世人:纵欲的下场是灭国亡家,遗臭万年。在这样的性文化阴影下,女性的天然欲望就更是要被灭绝除净。如果女人不能成为贞女节妇,就只能沦为淫妇荡妇,遭世人唾骂和鄙弃。由于中国女性历来受到更为残酷的礼教束缚和人性压抑,在屈辱的生存环境和非人的命运摆布中,形成中国女性卑贱的奴仆心态和畸形的性爱意识,因而在两性关系中,“女为男用”“传宗接代”就成了女性身份的定义,为了保全这一卑贱的身份,女人无条件地服从男人、伺候男人,并且还得曲意逢迎、讨好男人。近百年来,尽管腐朽的封建文化不断受到深刻的批判和清算,但是,令人遗憾和失望的是,在当代一些著名作家笔下,却依然缠绕着幽灵般的“古典情怀”,肆意践踏扭曲着女性的生命欲望。我们从《废都》、《苍河白日梦》、《神嫖》等文本中又看到了泛滥淫乱的性心理或性行为,看到了贞女荡妇们的现代演绎,却看不到作家面对畸变的两性关系及两性关系中女性的生命本相而引发的人文关怀及深度思考。
在这样一种陈腐而又暧昧的性文化背景中,王安忆与铁凝的超越意义便凸现出来。她们站在女性的叙事立场上观照着两性关系中女性生命的原生态与被动态,使我们看到女性天然欲望的蓬勃生机,她们在压抑中苏醒、膨胀、奔突,灿烂而美丽;但却在释放中被践踏、被扭曲、被窒息,在宿命般的命运轮回中承受一切,付出一切,在母性的皈依中繁衍和发展了人类。于是,我们也在这样一种尖锐的痛苦和无奈的悲悯中体味出作者对女性身份的反省和认知,以及这种反省与认知下面所汹涌着的人文主义情怀。
《棉花垛》中的米子姑娘靠了美色去钻窝棚挣棉花,在封闭而极端落后的农村经济条件下,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儿,就这样沦为出卖青春和美丽的工具,然而在付出了一切之后,她得到了怎样的人生回报?不过是随便地嫁个鳏夫,“不到五十就弯了腰,身上干枯得像柴禾。”更为可悲的是,米子的女儿小臭子还在“过家家”的童年,就会玩“勾引”男人的游戏了。“工具”的角色就是这样承传下去的。虽然,日本人的入侵,使小臭子一代女青年没能钻成花地;突如其来的民族战争打破了闭锁停滞的乡村经济,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也多多少少改变着人们的思想与观念。但历史的变迁是否给女人的命运带来了根本的转机?小臭子学着“八路”的样子穿紫花大袄,去夜校听课;她的女友乔则坚定地投身革命,成了积极干练的妇女主任。但这两位年轻女子却并不能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到革命与女人地位改变的本质联系,因而她们的追求和行为依然带有盲目性和蒙昧性,依然无法摆脱对男人的依附心态和被支配的从属地位。所以乔因为爱着抗日干部国而愿意为他积极工作,国一旦离开就觉得“心里没了主心骨”;小臭子虽然倾向革命,具有反封建的叛逆意识,但她骨子里“夫贵妻荣”的欲念使她傍上了日本警备队的秋贵,并为了秋贵,不惜出卖乔,成了可耻的女汉奸。最后,这两个女子都被毁灭了:乔被一群野兽般的日本兵轮奸后,用刺刀剜去乳房,挑开胸膛,死得惨不忍睹;小臭子被清算汉奸的国捉拿之后,竟先被国占有,再被处决,一个愚昧胡涂的生命便被结果了。这不能不让我们对于女性的性别悲剧和人生苦难产生更复杂更深广的忧患。
我们从《麦秸垛》中两位女知青的情爱悲剧中,依然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对女性性心理的畸形渗透,看到男权意识顽固地潜伏在现代文明背后,野蛮地剥夺了她们的幸福、扭曲了她们的人性。杨青与沈小凤都爱上了陆野明,虽然爱的缘由和方式大相径庭,但目的是一致的--最终嫁给这个男人。杨青作风正派、品行端正,言行举止都符合道德要求和社会规范。她追求志同道合的婚姻,并且要在不断的“考验”中检验追求的对象是否终身可靠。于是理智的她并不急于明确与陆野明的恋爱关系,而且还常常正儿八经地制止陆野明的欲望冲动......结果在不知不觉间用传统美德摧残了自己天然的情欲,而压抑的人性却也在不知不觉间积蓄了恶毒。所以,面对沈小凤的挑战,她不是用更热烈的爱去争取陆野明,而是怀着阴暗的心理希望、等待、促成陆野明与沈小凤之间“发生点什么”,借此报复他们。虽然回城后她与陆野明逐步接近了婚姻目标,但她得到的,却是在精神上阳痿的男人。相对于杨青的传统,似乎沈小凤具有着大胆反叛传统的精神和行为,她喜欢陆野明,就不管不顾地粘上了他,明知他“腻歪”她,也毫不在乎;当情欲不可遏制的时候,她任其迸发,在麦秸垛下偷尝了禁果。事发后,面对难堪的审问和舆论,她毫无羞耻之感和悔过之心。但悲剧的症结在于:沈小凤的骨子里没能摆脱的恰恰也是对男人“从一而终”式的依附,以至于胡涂而可笑地跪在陆野明脚下请求给他生个孩子。在普遍性的男权文化规范里,女人的归宿就是妻子和母亲,一个女人一旦与一个男人发生了性关系,似乎就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荒山之恋》中那个从小生活在“叔叔们”的宠爱与呵护中的金谷巷女孩儿,耳濡目染,从她妈妈那儿学来一套套摆制男人的心机和手腕,出落得美艳而又风流。但出人意料的是,尽管母女两代人都靠了性角色周旋于男人世界,却又可笑地恪守着“贞操”观念:女儿小小的心里就知道,女人要守好最珍贵的“宝”,“别的都可以玩玩笑笑,唯独这个不能松手。”因此,怎样“把个男人捏得滴溜转”,“女人身上的法道多着呢,守住那最宝贵的,也可算作一项法道了。”她们自以为守住了女人的“宝”,就有了左右男人的“法道”,从而就能拥有“女人的尊严和价值”,殊不知,如此的性功能里却充斥着男权文化的陈腐气息。男人向来把女人视为泄欲的工具,但他们又轻侮失去贞操的女人,于是要求女人们带着人性的枷锁为他所用。金谷巷女子正是自觉地带着人性的枷锁,把性功能当作征服男人的法宝在男人们中间施展着自己的魅力。最终,她的心机和魔法都没有白费,她征服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标准的男人,并把守住的贞操献给了这位终身依托的丈夫。然而,作为一个性情风流、争强好胜的热情女子,她最真实最强烈的生命冲动和欲望事实上一直在枷锁中被压抑着、捆绑着,特别是婚后又被“爱”她的丈夫策略地监控着。于是不甘寂寞的她便注定要遭遇一场毁灭性的性爱悲剧。她与大提琴手从开始的逢场作戏到弄假成真后的生死之恋,意味着她“灵魂和欲念的极深处的沉睡,被搅乱了。”于是,她象燃烧起来的野火,疯狂地不顾一切地燃烧下去,直到把两个人的生命燃为灰烬。
《荒山之恋》作为“三恋”中写得最早的一篇,作者对婚外恋的态度尚有几分谨慎和隐约存在的道德谴责,故在叙事结构上,男女主人公的恋情发展与命运结局,似乎过多地依赖了性格因素和戏剧性巧合,这多少削弱了作品人物深层的生命本相展示。同样是写婚外恋,《锦绣谷之恋》就完全换了一种叙事观点,作者将叙事视角直接移植在女主人公的主体意识中,却又采用客观的第三人称写法,这既缩小了叙事者与被叙事者之间的距离,使人物命运更接近主体意志;同时又拓展了读者与被叙事者之间的空间,使审美过程中有了介入的可能,从而产生非限定性的审美判断,作品的意蕴便获得了多向度的张力。所以,从外部结构看,小说叙述了一个婚外恋故事,但随着叙事视角深入,却发现这是女主人公感觉的无限夸张和神秘化过程。一个终年困守于常规秩序和乏味厌倦的家庭城堡中的知识女性,在如诗如画的庐山邂逅了一位有才华有风度的男作家,于是产生了繁复多姿而又细腻曲折的情爱梦幻,使她再次经历了初恋般的诗意和痛苦,并在一种近乎自恋的臆想中,重新向往灵与肉的和谐与沉醉,向往着女性意识中完美的生命境界。然而,当庐山虚幻的大雾渐渐退去,人生的现实真貌便无情地裸露出来。她还是她,日子还是日子,秩序还是秩序,不可逆转的人生滋味无穷尽地在文本之外弥漫着、缠绕着,人人都别无选择,虚无和荒诞感油然而生。
4、关于“母性”
基于对女性生命悲境的深刻体验和理解,王安忆与铁凝也在积极探寻女性的自我救赎之路,但她们却有意回避了极端的女权主义色彩的书写,因而也就不致于为了抗争女性的不幸而陷入“女人中心论”,在自哀自恋的情节中难以自拔;或以“女性雄化”去反叛“女性奴化”,以凶悍粗犷的“女光棍”形象取代柔弱温顺卑贱的“女仆人”形象。相反,她们共同以悲悯却又崇敬的目光重新发现、审视着女性身上天然未泯的母性及母性中所有的利他主义情怀。显然,解读王安忆与鉄凝,不能站在纯粹的女性主义立场上,而应该在一个多维的审美空间,给予更博大的人文主义精神观照,从而去把握她们对女性生命本相的阐释。
王安忆在《小城之恋》中,用过于铺张的笔墨叙述了一个歇斯底里的性爱故事:一对青春男女自小一起练功、厮混,随着性意识的萌发和骚扰,他们象两头野兽一样在原始的性驱动下,互相渴求,互相发泄,互相折磨。疯狂而野蛮的性行为使他们在罪恶感的煎熬中彼此仇视,消蚀着青春、尊严和生活信念,最后带着绝望的情绪自暴自弃,沉沦于无比痛苦的深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对年轻人的绝望代表了人类普遍性的绝望--在强大无比的欲望折磨和支配下,命运的不可抗拒和不可把握;人性找不到出路的莫大悲哀与恐慌......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文化心理积淀,培植出多少不敢正视自身生命原动力的猥琐人格,使他们不仅不能以健全的心态认识、崇拜生命之动力,反而以肮脏、丑陋的方式肆意践踏、毁坏着生命冲动,因而才衍生出无数畸形变态的性心理和性行为。所以,作者在叙述这一对男女的放荡和沉沦时,就故意抛开了社会道德的审视目光和批评尺度,并且故意让意外的受孕来结束他们的痛苦挣扎,唤醒了女性生命深处的一片圣地。母性的苏醒使女主人公从一个浑浑噩噩、蒙昧简单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丰富的女人,生命因而获得了延续下去的意义,这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却不得不承认,惟有母性的力量才能够起死回生,拯救人类。
铁凝笔下的大芝娘(《麦秸垛》),大模糊婶(《青草垛》)都是十分母性化的典型。大芝娘“身材粗壮,胸脯分外地丰硕”,浑身洋溢着成熟的生命气息。可是大芝娘新婚第三天,丈夫就骑着骡子参军走了,多年没有音信。大芝娘恪守着妇德、忍耐着寂寞,苦守苦盼着,谁知最终盼回来的,是提了干部,有了新欢,说着满口大道理要与她离婚的男人。认命的大芝娘同意与丈夫离了婚,却又不认命地追到城里,要求跟男人生个孩子。她并不觉得带个没爹的孩子会拖累自己,也绝对不会再有追求幸福的念头,这是她的命,她就得听任命运的摆布--千百年来的妇女都只有这一条命,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大芝娘还能有什么不平与怨艾?所以,能有一个孩子就不算“白做了一回媳妇”,就有了活着的希望和信心。果然,当孩子出生后,大芝娘一颗心“彻底踏实了”,她不要男人分文,没命地劳作,一手将孩子拉扯大,甚至在困难时期,把男人一家接来供养,“直把粮食瓮吃得见底......”长大成人的女儿死于非命,几乎将大芝娘彻底击垮,虽然她把无私的母爱继续施予知青和没了娘的孩子五星,白天依然颤动着一双肥奶猫腰在地里劳作,但在漫漫长夜,只有“低沉的纺线声”如泣如诉;那个被她抱得发亮的长枕头,沉重地陪伴在她生命的尽头。大模糊婶也象大芝娘一样,是个身体硕壮、心地宽厚、头脑简单、性格泼辣的农村妇女,但也命运不济,没了男人,孩子也死了,年轻轻的时候就孤身一人。尽管她赶上了商品经济时代,偏僻贫困的小山村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大模糊婶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观却没有发生丝毫改变。她对一落地就死了娘的一早胜过亲娘,用那一对“大被窝”似的乳房哺育他、呵护他。当人们撺掇她与一早爹搬到一块儿住,他们却谁也不同意。于是这寡妇、鳏夫、孤儿构成了一个奇特的亲情世界--这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仁义道德世界。这位大模糊婶曾无所顾忌地在年轻闺女面前展示自己的私处,以炫耀做过媳妇、生过孩子的女人的能耐;当这不雅的“大模糊”婶从此叫响,常有人来打趣讨便宜时,她仍然大模大样,毫不在乎。那么,这位貌似开放、轻佻的女人能够在粗俗的笑闹中排遣寂寞,为什么就不能在正常的两性关系中追求新的归宿、满足自己旺盛的生命欲望?显然,大模糊婶也清楚地知道,这是她的命。对于大芝娘、大模糊婶这类传统女性来说,丈夫是她们从一而终的依靠,生儿育女是她们全部的人生意义。当这依靠失去,能够使她们坚韧地活下去的动力就只剩下无私的母性了。
5、对男权文化的批评及作家的女性意识
在母性博大、无私、牺牲的圣辉下,总是能洞照出男人狭隘、自私、索取的功利心态。王安忆和铁凝虽然没有站在女权主义立场上任意贬损男人,但当她们本着人文主义关怀去注视与女人发生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男人群体时,还是掩饰不住失望与鄙夷的目光。
王安忆善于从文化心理积淀上发现男人的性格缺陷和先天不足,目光颇为尖刻锐利;铁凝则习惯于从现实社会关系中凸现男人的行为弱点和道德伪善,态度比较含蓄温婉。所以,在“三恋”中,有的男人生着一张老相的脸却长着个“孩子的形状”--象征了中国男人心态的幼稚、人格的萎缩;有的男人孱弱、自卑、无能,拿不出一丁点的男子汉气概,这是在女性滋养呵护下“未断奶”的男人;有的男人唯唯诺诺、麻木漠然,在琐碎的现实生活中丧失了个性与热情,是近乎阳痿的男人。在“三垛”中,我们看到大芝娘的丈夫参加革命衣锦还乡时“说着一口端村人似懂非懂的话”,与大芝娘谈妥离婚事宜后“一早就慌慌地离开端村”,待大芝娘追到城里要跟他生个孩子时,“他和她睡了,但没有和她细睡”;我们还看到那些在棉花地里靠几斤棉花就可以任意玩弄女性的男人们“早早把窝棚搭起来,直到霜降以后......还拖着不拆。拖一天是一天,多一夜是一夜”;那个带女汉奸去敌工部听审的国“拱着小臭子心口上的汗,手抓挠着小臭子的腿”,意犹未尽地“想起有些书上不堪入目的木版画:这样的,那样的......”然后要求小臭子“来个这样的吧”,“太阳只剩下半杆高时,国才穿好衣裳坐起来......”“国穿好衣裳,系上皮带,从枪套里掏出枪”,“他瞄准小臭子的头,手指抠了一下扳机......”;那个在马蹄梁翻车身亡的冯一早,由于阴魂不散,便得以窥探到更多男人的隐秘行为:虚张声势的,蝇营狗苟的,无耻放荡的......铁凝淋漓尽致地揭示出男人--“行动的动物”本相,充满了反讽意味。
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波伏娃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的。”这意味着女性研究已超越了生物性别上升到女性的文化内涵。正因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一系列的文化规则所塑造的社会角色,因此对女性文化身份和处境的探讨、追问,对女性在人类文化中的命运及男女权力关系中的困境的关怀与书写,构成了文学中的“性别立场”--即所谓的“女性意识”。王安忆和铁凝的“三恋”“三垛”正是通过“性” “母性”,反省女性的文化身份,因而具备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性别意识”。然而,基于对文学一如既往的认真,王安忆和铁凝都特别注重对生活经验的多层次开掘。因此,她们对女性身分的反省与人文关怀,就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与层面上,联结起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与历史、文化、民族等内在的密切关系,这就使她们远远超越了那些刻意标榜女性写作而将自己封闭于私人空间的女作家们。
第四阶段
1《纪实与虚构》 1《玫瑰门》
2《伤心太平洋》 2《大浴女》
3《叔叔的故事》
4《长恨歌》
5《富萍》
《玫瑰门》以一个童年的女孩荒芜而喧嚣的岁月中,生涩迷茫地穿过人生的玫瑰门为线索,在全知叙事人视点中连贯起婆婆司猗纹这个“永不定格”的女人的一生,它的人物展示了一个女人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却没有温馨、也没有欢乐、也没有幸福,有的只是丑恶、卑琐、压抑和痛苦。作者一方面开掘了历史的烟尘和现实的污垢掩蔽下的女性生命特有的柔韧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开掘出了女性生存状态中与女性相互关于特有的狡诈、卑琐和丑恶。
它真实展示了“一种女性的状态,女性的生存方式和一种生命过程。”我们看到的是被历史重负和现实的压力挤压扭曲变形的女性的灵魂。
提示:王安忆对“弄堂”文化的深入探寻,对“城市与女人”关系的书写;铁凝对女性成长与历史场景内在联系的观照与展示
第四节 女性激愤的呼声:《方舟》
张洁小说中痛苦的理想主义者自我形象的刻画。对社会异化状态下知识女性精神痛苦和生存命运的关注与写照。
(一)、对美的讴歌及理想抒情。
张洁是带着对美的向往和理想色彩步入文坛,这与她的童年经历有关。她是“穷人家的孩子”,有过寂寞的童年,但一架破风琴和几本破书闯进了生活,她如同一朵在冰天雪地里做着梦的雪莲,“在寂寞中开始不寂寞的生活”试图用幻想和想象来重新安排周围的世界,“觉得文学给予人们的,要比生活给予人们的多,”“书里的人们似乎离我更近,让我觉得更容易理解,我真愿意生活在书里,永远不出来才好。”可见,张的审美理想不是在对现实的切入而是对现实的离开中形成;形成这种理想的时候,其营养的食粮更多更好地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文学。因此,她的创作之初,就带着主观色彩较浓的诗意光芒。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寻求》
张洁的创作与“伤痕文学”形成对照:当大多人更多反省过去,她却展望未来。别人在清算历史的丑恶时,她在讴歌理想的美好;别人在进行社会的批评时,她在进行新人的设计。她以娟秀清丽的抒情文笔展望着一种新鲜迷人的魅力。
(二)、对爱的追寻与失落之伤愁--创作的一个高峰:痛苦的理想主义者探索
“爱”与“人”的主题:《方舟》对知识女性爱情的破灭,家庭的不幸给予超越《爱》的现实审读,笔调的抒情转向怨诉。但这些作品深深饱含作者对于理想爱情的美好人性的执著追寻,又因它似在现实中扭曲、失落而弥漫一层浓浓的伤感色彩,构成张洁独特的“痛苦的理想主义”。
思考与练习
1 张贤亮的作品表达了怎样的人道主义情怀?各有什么特色与侧重点?
2 《哦,香雪》表达了怎样的诗意?背后寄予了作者对时代现实怎样严峻的思考?
3 《方舟》所表现的现代知识女性的人生困境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