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
作者:黄 伟
改革伊始,坚冰还未打破,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是政策所不允许的。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张“生死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按传统方式摁下了鲜红的手印。小岗村“大包干”一举成功。可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政策都没有规定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禀性率真的王郁昭为争取上级支持和政策的许可,形象地呼吁为“大包干”上户口!
黄:您说的这三个典型中没有提到小岗村,请您谈谈小岗村为什么会闻名全国?
王:1979 年, 随着包产到组的发展, 一部分生产队也在暗中搞了包产到户。这其中, 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以严宏昌为首摁下18个鲜红的手印,首创了“大包干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到户”是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新生事物, 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由此奏响了中国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突破的华美乐章。上个世纪50 年代就出现过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在分配过程中往往出现“一平二调”和干部中存在某些不正之风等现象, 群众很不放心, 实际上农民对产品没有支配权。而“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则不同, 农户承包集体的土地后, 由生产队同农户签订合同, 农户按合同上缴国家的征购任务, 交足集体的提留, 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奖赔就在其中了。用农民的话来说,“大包干、大包干, 直来直去不拐弯, 完成国家的, 交足集体的, 剩多剩少全都是自己的”。“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 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 而农民通过承包则取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 即经营权。这种方法既能保证国家的税收、征购和集体提留任务的完成, 又使农民取得了生产自主权和产品支配权, 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大包干”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很快普及开来的关键所在, 也是人们所说的“凤阳之路”的核心。
当年,我特地组织县委书记和地区各部委科局以上干部到小岗生产队,开了个不讲话的现场会,从西到东挨家挨户看,看群众家的粮囤子,同群众交谈,大家受到很大的震动。1979年的实验结果是,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有12户粮食超过万斤,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社员收入比上年增长6倍。2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油料,分别超额6倍和80倍。地委对小岗生产队的做法进行调查和剖析, 对“大包干到户”给予肯定,当时曾批准他们继续试验,再干3 年。
黄:我们注意到2007年9月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了《为大包干报户口的人——王郁昭》,这部书书名很特别,“报户口”的意思何在?
王:在1980 年初省委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 我做了题为《顺应民心, 积极引导》的发言, 并要求给“大包干”报个户口,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我认为劳动者的积极性高与低, 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志,实践证明“大包干到户”责任制就是让农民穿上了“合脚鞋”, 因而中国的农业才能跨大步。万里在会议总结时坚决支持我的意见,他指出:“‘双包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 问题是已经有了, 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她妈妈挺高兴, 哎呀, 可解决大问题了, 你不给她报户口, 行吗? 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 孩子挺好的, 给报个户口吧, 承认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 ‘双包到户’不等于单干, 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 没有什么可怕的。”省委终于同意给“大包干”报上了户口。但是这个户口还是地方户口, 只能在安徽省通行。
只要对得起党, 对得起老百姓,
就问心无愧!
自古以来,改革都遇到过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阻力,滁县地区的“大包干”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阻力,当事人王郁昭最为清楚。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他执著地表示只要对得起党, 对得起老百姓,就问心无愧!即使丢掉“乌纱帽”也无怨无悔,展现了一位改革家无所畏惧的胆略和气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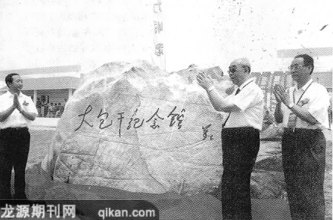
黄:看来滁县地区的改革比较顺利,是这样吗?
王:任何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双包到组”(包产到组、包干到组)责任制的推行伴随着激烈的争论。1979年3月1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围绕联产计酬,对包产到组、到户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对安徽包产到组形成了围攻之势。反对者认为这种责任制不符合“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原则。
更为严重的是,1979 年3 月15 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甘肃省张浩写的一封读者来信, 标题是《“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应当稳定》。来信认为,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 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 是脱离群众的, 是不得人心的……报纸加了编者按, 提出要“坚决纠正”。这对“双包到组”后正在忙春耕的皖东农民来说, 无疑是泼了一瓢冷水。一些对“阶级斗争”心有余悸的同志, 认为编者按有“来头”, 惶恐不安。针对干部群众思想上出现的波动, 地委及时向各县发出电话通知, 明确指出:“当前正值春耕春播大忙季节, 各种形式责任制一律稳定下来, 不要变来变去, 延误农时。”“各种形式责任制是地委同意试验的, 如果错了, 完全由地委负责。”各县县委态度坚决,凤阳县委书记表示:我们是王小二盖猪圈,决心门朝南,坚决不改变。嘉山县委书记表示:“春耕已经开始,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这时,万里来到滁县地区视察工作,他说:“作为报纸, 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 别人写读者来信, 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这好比公共汽车一样, 你可以买票上车, 我也可以买票上车。”“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靠实践来检验, 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 就打退堂鼓。”“产量上不去, 农民秋后饿肚子, 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 报社是不会管饭的。”他还说: “你们地委做得对, 及时发通知, 已经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动, 只要今年大丰收, 增了产, 社会财富多了, 群众生活改善了, 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 后年还可以干, 可以一直干下去。”张浩来信引起的这场风波被平息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80年1月11日—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会议,当安徽代表在会议上作了《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的发言后,再一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与社会主义沾不上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如果不制止,社会主义阵地就丢了,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次会议由于是部门召开的,安徽省委没有传达贯彻,对安徽的农村改革没有发生影响。
黄:据说,万里离开安徽之后,争论更加激烈了,是这样吗?
王:1980 年春, 万里离开安徽调中央工作。风云突变, 围绕“大包干到户”的争论在全省乃至全国迅速展开。从1980 年上半年开始, 安徽省委新的领导人,一反常态,反对联产承包制,马不停蹄地连续召开了蚌埠、芜湖、巢湖会议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这些会上,“双包到户”被扣上了“经济主义”、“机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大帽子,特别是反对大包干到户, 说它是“两包一脚踢”,不是集体经济的统一分配。在上述三次会议的影响下,全省农村改革的形势急转直下,政治空气骤然变冷, 搞得人心惶惶, 有的县急急忙忙下禁令不许搞包产到户, 搞了的要限期收回。这时, 只有滁县地区坚持不动,实际上成了一个“孤岛”, 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就在这关键时刻, 在巢湖会议上, 省委领导给我看了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他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 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 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 也是一年翻身, 改变面貌。”这个谈话, 在我国农业面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 拨开了迷雾, 指明了方向。我振奋不已,回到地委后, 迅速向各县委书记作了传达。在小平同志谈话精神指引下, 滁县地区的大包干责任制, 迅猛发展, 继续破浪前进!
黄:小平同志讲话之后是不是没有争论了呢?
王:虽然小平同志的谈话满腔热情地支持了双包到户, 但争论并未结束。1980 年8 月在省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除滁县地区、六安地区外, 会议基本上是“一边倒”, 形成了对“双包到户”的围攻之势。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得不站出来讲话。我首先强调: “双包到户”关键是一个“包”字, 它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劳动者积极性高与低, 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双包到户”不是单干, 是集体经济在管理体制上的新突破。接着我列举了来安、定远、凤阳等县实地调查的数字说明, 增产最高的是“双包到户”, 次之是“双包到组”,平产或减产的是坚持“大锅饭”的生产队。结论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我恳切要求, 由于滁县地区“双包到户”的面很大, 而且还在发展, 实践证明是能够增产的, 希望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 继续完善提高。如果上级领导不同意, 那就请上级正式发个文件, 进行纠正, 我作为共产党员、作为下级,服从就是了。不要像现在这样, 今天这里批,明天那里批, 施加压力, 搞得人心惶惶, 整天提心吊胆。我已准备被撤职, 但问心无愧,对得起党, 对得起老百姓。当时会场气氛紧张, 意见分歧很大, 最后省委书记顾卓新建议把小平同志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那篇谈话念了一遍, 作为会议的总结。
黄:如此看来,对于“大包干”的争论还是十分激烈的。究竟是什么时候结束了争论呢?
王:1980 年9 月27 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接着又连续五年发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 正式给“双包到户”报上了户口, 明确“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生产责任制。由此, “双包到户”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 到1983 年全国“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了98% 以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我国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1993 年3 月, 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决议, 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载入我国宪法。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突破的,确实是来之不易的。(责任编辑 汪文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