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童话中的精灵与现实中的悲悯
作者:江 冰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海阔故事汇
也许,所谓“哲理”,只是批评家的臆想,学问家的总结,作家本人只是在生活中发现并感悟,再用小说的方式将其传达出来,类似米兰•昆德拉随时从世俗日常生活中焕发出哲思的光彩,也仅仅是他的一个路数,迟子建自有迟子建的方式,但她在此部作品中“发现”流程中所刻画的人物关系,又的确可以使得我们将思考深入到男女爱情与婚姻的人类普遍性问题里去。优秀的作品总有可以解读的多个层面,而表层可读与深层可读又常常是那么自然地过渡与融合。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艺术上的成功取决于两种融合: “情感”与“发现”之流的融合,表层可读与深层可读的融合。
三、哭者与歌者:主角的登场与谢幕
哭者,蒋百嫂;歌者,陈绍纯。两个乌塘镇的主角是作者着力刻画用心最多的人物。两个人物的苦难人生为作品确定了悲怆的基调,奠定了作品的社会内容与文化立场,也为作品“我”的情感升华做了充分的铺垫。
先说哭者。蒋百嫂是作品的核心人物,是推动乌塘镇故事发展的枢纽。迟子建刻画这个人物分了三个步骤:出场前的渲染,荡妇闹事,家中揭秘。作为小说家,迟子建充分地体现了高明的叙事策略,她用足了笔墨,耐心地渲染,沉着地铺垫。未见主角,先见她的儿子和她家的狗,儿子有难以解读的忧郁眼神,狗为主人蒋百已成一条寻找谜底的丧家之犬,谜局设了下来。随后,蒋百嫂闹酒馆、闹停电,且已成为乌塘镇的新闻人物,人皆可夫,放荡不羁,既烈如野马,又悲如残月。正面、侧面、耳闻、目睹,种种反常表现,更增重重迷雾,悬念让人期待答案,乌塘让人期待真相。沉默的冰山在“我”的探秘中显露真相,悲剧由此走向了顶端,也走向结束。值得一提的除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之外,还有作者社会批判的方式,在真相暴露时,作者并没有呼天抢地、义愤填膺,而是转而悲悯;“这种时刻,我是多么想抱着那条一直在外面流浪着的、寻找着蒋百嫂的狗啊,它注定要在永远的寻觅中终此一生了。”也许迟子建清楚地知道,批判社会并非小说所长,而悲悯生命才是作品之所寻求。然而,作品的社会批判力量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一种情感的震撼显然已经传达给读者。仿佛这位充满巨大生命愤怒的哭者,唯有在凄美的民歌声中短暂地找到宁静,读者也由此看到一种生命的释放。
再说歌者。如果说哭者蒋百嫂代表一种民间现实的话,那么歌者陈绍纯则代表一种民间历史,陈绍纯的形象刻画是与蒋百嫂交叉进行的,两者的精神联系清晰可见。陈绍纯是乌塘最有文化的老者,从人物刻画着墨上看,不如蒋百嫂,生动性也略逊一筹,人物成长也多用交代性叙述。但就其人物抽象意义上看,他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又有高于蒋百嫂之处。况且,作为蒋百嫂形象的精神补充,又从历史纵深与文化底蕴方面丰富与深化了乌塘人物形象。假若删去这一老者形象,乌塘人就可能成为乌合之众,就可能在丧失民间文化“文革”劫难等历史记忆的同时,变成苟且偷生的行尸走肉。作品的现实感历史感文化感也将大打折扣。在我看来,陈绍纯的形象塑造是很有点符号化的意味,中国作家历经十年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洗礼,世界文学的众多方式与技巧已经水乳交融地体现于当代小说创作之中,尽管我们也可以在曹雪芹的笔下找到相呼应的痕迹,但毕竟在21世纪初的中国,全球化浪潮里的中国小说家已经拥抱了世界,细说文本,多处象征意味有迹可寻:“幽长的巷子”犹如历史,“回阳巷”的名称好似民间文化的回光返照;面容清癯的老人在“画荷”,荷花“没有一枝是盛开着的,它们都是半开不开的模样,娇弱而清瘦”;歌声如倏忽而至的漫天大雪一样飘扬而起,没有歌词,只有旋律,那么悲怆,那么寒冷,又那么纯净;因为濒死体验而痴迷凄婉的旋律,因为“文革”受辱吞食歌本而恢复的民歌记忆。为了这种“符号性”,迟子建不惜将其擅长的童话笔法强化至魔幻的地步:有一回他唱歌,家里的花猫流泪,还有一回他唱歌,小孙子撇下奶瓶,从那以后不碰牛奶了。为了这种“符号性”,作者“无情地”迅速将笔下人物的生命了断于沉沉的暗夜之中,并让那些失传的民歌无声无息地随歌者而去,永久地消逝在人世之间。陈绍纯老人的猝然离世,表达了一种悲剧性的归宿:乌塘最有文化的人消逝了,犹如传递千百年的民歌彻底地失传了!造成这种命运的原因是什么呢?作者并没有明说,而是颇有象征意味地安排了一个近于荒诞的情节:被艳俗的牡丹图镜框砸死了!画者死了,玻璃碎了,但画却纤毫未损,“红色的红到了极致,粉色的粉得彻底”。陈绍纯老人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他是在掩埋自己吗?至纯至美的悲凉之音,幽长逼仄的回阳小巷,单薄而阴冷的阳光,娇弱而清瘦的荷花一旦演变成又红又粉的牡丹,歌声便戛然而止,画者即溘然长逝。民间的悲苦与苍凉,文化的执拗与不屈,于回阳巷老人的生命焕发出灿烂的一刻。歌者永远的喑哑与冰山无法永久的沉默构成一种看似反差却蕴含内在联系,一种具有生命爆发力的联系,在迟子建看似轻柔委婉的描写中其实含有一种令人害怕令人颤抖的危险张力,冰山的一角预示着冰山的巨大的容量,激愤的哭者与凄苦的歌者将汇合成怎样的洪流?!就此,迟子建通过作品完成了现实层面与哲理层面、世俗层面与灵魂层面、人物层面与符号层面的双向书写,它们既交叉互补又各自独立,共同完成了作品艺术结构与艺术意蕴艺术传达,使作品表层可读性与深层可读性近于完美地合为一体,看似老套的情节被重新焕发了新意,不同层次的读者也从中得到各自满意的收获。
四、结语:双重人格的北极精灵
双重人格是一个用“滥”的老词,但我还是愿意以此来分析我眼中的迟子建,她的第一重是童话人格,属于北极大自然的精灵,童话诗人,自然崇敬,靠心灵与感官逍遥于自然,亲近那片大地是她的本性,也是她作为小说家的资本与潜能;第二重是现实人格,它参照第一重而存在,面对人世,她是智慧的、冷静的、独立的,两重人格造成巨大反差,童话的纯美与世俗的繁杂,在并无明显宗教倾向的迟子建那里,形成一种悲悯的情怀。悲悯使她比社会批判性的小说家超越一点,而童话的纯美又使她在内心在作品里形成更为强烈的反差,反差促成认识,促成表达,于是焕发出对于中国现实生活非同一般别出一格的艺术传达。反差愈强,情感愈烈。值得羡慕的是,此种艺术传达,无论在世俗还是灵魂层面,迟子建都是比较成功的。话说回来,双重人格也可以平白地表述为童话中的精灵与现实中的悲悯,唯其如此,迟子建出类拔萃,“独一份”逾日凸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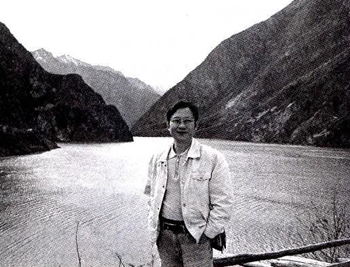
江冰,中国小说学会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出版《文学评论的阐释》《浪漫与悲凉的人生》等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逾100万字。《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20余篇。多次获全国奖及省级各类成果奖。为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评委、中国小说学会奖评委。曾任《创作评谭》杂志主编,现为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