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个人记忆的温暖回归
作者:谢 琼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海阔故事汇
温情的笑意
身体的记忆,总是温暖的。对于用身体记住的东西,人们总是充满爱的,因为那已成为自己身体上无法割舍的一部分。这正如林白在《致一九七五》中所引用的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对林白来说,她对那所有通过身体记住的欢愉或苦难,也已经无法用理念或逻辑来判断对错,而是无条件地充满深情。正因为如此,书中对于过往生活的回忆,常常带有一种愉快的调侃,令人发笑。例如,书中有这样长长的一段话,那是作者描写刚上小学二年级的李飘扬如何要给语录歌编舞蹈动作以便上街头演出的过程。语录本身是这样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关于编舞,作者这样写道:
我想了一天一夜,还是没有给这条语录歌编出动作来,头都憋疼了。我像一个学打哑语的人,不停地做出吃饭、写字、绘画、绣花的具体动作。不用说它们根本不是舞蹈语言,也不是体操,根本就是奇怪的哑语。……下文的“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也让我一筹莫展。倒是结尾好办,时代的最强音,“革命是暴动”,双手握拳,高举过头顶,两脚并拢、绷直、踮起,“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双腿迅速变成右弓形,右手握拳高举过头顶,左手握拳直击右下角。不用说也能想到,这是一个传统戏剧里武松打虎的经典姿势,正好暗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意思。……
如果读者愿意耐心地跟随林白的笔想象那一个个肢体动作,一定会像我一样咯咯地笑出声来。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滑稽的场景,单独看来仿佛是对那个失去激情而徒有形式的后革命时代的强烈反讽,放在书中却只让人觉得温馨可爱。在另一处,在谈到70年代电影时,作者则直接表白了这种不合理的喜爱之情:“所有这些,70年代中期的国产片,艺术上那么粗糙生硬,充满了可笑而奇怪的政治,当时的有识之士和现在的人们,一眼就看出这是垃圾,但我为什么不知道呢?我喜欢这些垃圾,我觉得它们生机勃勃,它们生长在我十四五岁的日子里,被青春赋予了光芒,年轻的沃土肥力无穷,一片塑料都能生长出森林和原野。”对过去岁月无法割舍的切肤之爱,使作者行文中的幽默和反讽别具一格,它们不尖酸刻薄,不振聋发聩,温暖而轻松,使作者既能以一种带有距离感的眼光回望过去,又并不必然走向对往昔岁月的彻底否定。这样一种温暖的反讽,不是对对象的绝对的否定,而是对矛盾世界的充满主观自由的把握,它使作者能够在正视过去所有的苦难和荒谬的同时,超越那些苦难和荒谬可能带给自己的伤痕。我一直以为林白作品中的幽默和反讽独具特色,从《一个人的战争》开始便是如此。我只想说,在《致一九七五》这本书中,不管是上部对儿时那些傻事的回忆,还是下部那漫不着边的狂想,作者的特有的这种幽默和反讽发挥到了极致。岁月和阅历使作者在面对过去时比从前更加游刃有余,更加宽容,更加爱。我们读着它,会和作者一样发出温情的笑,并且那温情会传遍我们全身。
通往过去的门
我说过,阅读林白有很多种方法。我在文章的开头罗列了数种,仿佛一个蹩脚的老师在教孩子们做阅读理解题。不过我总是固执地认为,对于林白的作品来说,如果总是要坚持弄清楚作者在这本书里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我们会错失太多。在我看来,《致一九七五》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能够通往过去的门。我们仿佛第一次发现,原来用感知和身体,也可以发现那么多的、并且是关于那么多人的过往,这种发现虽然也许只是记忆的碎片,这些碎片却终将拼成另一种往昔生活,它不同于书上写的、不同于别人说的、甚至不同于自己以为的那样,但又的的确确是真实的。阅读这本书,也就不仅仅需要眼睛,还需要身体,需要跟着作者所写的歌词哼上两句儿时的歌,或者跟着作者所描绘的食物咽两口口水。也许生于不同时代的我们无法体会到1975年歌声的激扬和食物的芳香,但我们将知道,我们的过往也正如林白的“一九七五”一样,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身体。在合上《致一九七五》的那一瞬间,我们将感到,我们的一九六五或是一九八五,也已经开始在我们身上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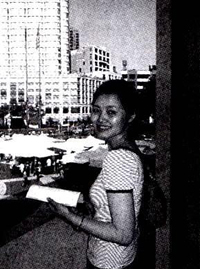
谢琼,出生于山西太原,10岁举家南迁南京,18岁北上北京求学至今。北京大学东语系本科、硕士毕业,荷兰莱顿大学文学理论专业硕士毕业,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博士在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