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借“无我”之翅,放飞“唯我”去野游
作者:王列耀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海阔故事汇
一个精妙的意象,有时同样可以照亮一篇好的散文,尤其是一篇好的诗化散文。经由 “无我”与“有我”的“灵手”“拿来”、创造,再经由“唯我”的情绪和情感的反复搓揉,不论是“借来”的,还是自我锻造的意象——以成群结队方式展现与组合的意象,正像天空中闪光的星星一样,以密集与幻化的方式不断闪耀着,既神奇又迷人。
三、放飞“唯我”的想象与叙述
在放纵着“唯我”的情绪,搓揉出种种“唯我”的意象的同时;钟怡雯更放飞着种种“唯我”的想象与叙述——让它们“如狐如鬼”地去野游。
种种神秘、丰富的想象,在《垂钓睡眠》中,往往突然而至、神出鬼没,而且如狐如鬼,贯穿全篇。
——从“谁下的咒语”“拐跑了我从未出走的睡眠”,到把“眠”想象为“跷家的坏小孩”、倦鸟;
——从把“睡”想象为被伤害、被遗弃的情人,到把“睡眠”想象为垂钓;
——从有饵无钩的诱饵,到用诱饵钓回睡眠;
——从把“睡眠”想象为猎犬与兔子、睡门与钥匙,到“急忙把那四颗梦幻之丸埋入昙花的泥土里”,“它们会变成香喷喷的诱饵,有朝一日再度诱回迷路的睡眠”。
这些丰富、“唯我”的想象,还具有如狐如鬼般的情感:枕头“雍容大度地容忍我的鲁莽和欺凌”,“闹钟催命似的鬼嚎”,“远处细微的猫叫,在听觉里放大成高分贝的厮杀”。这种“多情”的、近乎诡异的想象,既充分表露出一个失眠者急躁的心绪,也在急促的节奏之中,蕴含着一种神秘与迷人的美感。同时,这种“多情”的、近乎诡异的想象,还孕育着作者对生命经验的某些顿悟:“朋友一旦离开就像逝去的时间永不回头,他们不是身体的一部分,亦非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更不会像丢失的狗儿会认路回家。”
丰富、“唯我”的想象,往往还和“诡奇”、“惊异”的叙述,“如狐如鬼”地携手并肩:
睡眠的欲望化成气味充斥整个房间,和经过一冬未晒的床垫、棉被浓稠的混合,在久闭的室内滞留不去,形成房间特有的气息。
经过想象与叙述的共谋,失“眠”的感觉,未曾“摇身”,仅在“一室之内”就已“三变”——顷刻之间,先化作“味觉”;转眼功夫,又移位成了“视觉”。于是,抽象的睡眠,也就“摇身”成为一组“三维”的动态的图像:有“睡”无“眠”的“睡眠”,或者说是“睡眠欲望”——那有形无心的身影,是如何无奈、无望地四下张望,张望之后,又是如何可怜又无奈地“滞留”在“整个房间”。
丰富、“唯我” 的想象,往往还要和“诡奇”的叙述,“携手并肩,“如狐如鬼”地制造出一些意外与惊喜:
我以为是自己失眠的缘故。一日朋友来访,我关上房门后问:“你有没有闻到睡眠的味道?”他露出不可思议、似被惊吓的神情,我才意识到自己言重了。
“我”的发问,与“被惊吓”朋友的对接;发声者与接受者之间,出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错位”——不正常的状态中的正常的发问,变成了正常接受状态中的不正常的“暗示”—— 由“唯我” 的想象和“诡奇”的叙述,合谋的“暧昧”之气,瞬间就“拼接”出一种意外的惊奇。
放纵“唯我”的情绪,搓揉“唯我”的意象,放飞“唯我”的想象与叙述,以“无我”放飞“唯我”去野游;钟怡雯使《垂钓睡眠》具有了诗的想象、诗的语言、诗的情感、诗的美感和张力;也“以呼风唤雨”的才情,“如狐如鬼”的魅力,“为世间增添了一篇妙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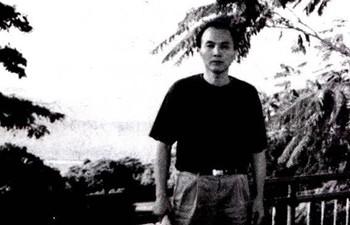
王列耀,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暨南大学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近年在《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的著作有《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隔海之望——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望”与“乡”》《宗教情结与华文文学》《困者之舞——近四十年来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