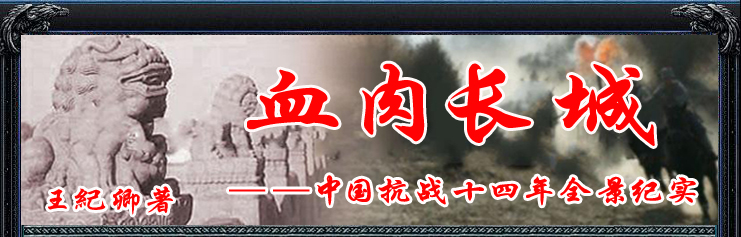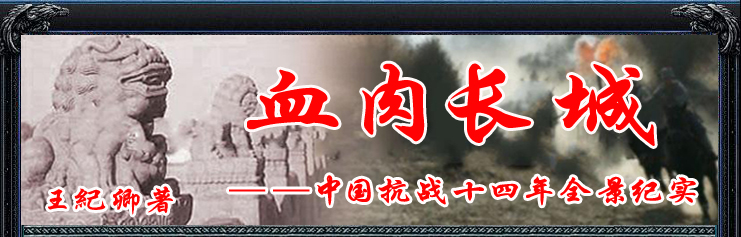|
|
日苏诺门坎事件发生后,北满的日军主力大部分调往边境,黑嫩平原的抗日斗争有了蓬勃发展的契机。活跃在黑嫩平原的各路抗联部队,需要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他们于1939年5月在得都县朝阳山后方基地成立了抗联第三路军,与抗联第一路军和第二路军形成犄角之势。三路联军摆成一个大三角形,更有利于配合全国的抗战。
中共北满省委指挥第三路军各部深入敌战区腹地,把游击战争从山边推向平原。黑嫩平原上掀起了抗日新浪潮。
冯治纲率领第十二支队在9月18日强攻讷河县城,乘敌不备,一举攻克了伪县署和伪警备队的北大营,活捉了伪军团长等一批伪官吏,打死日军十多人,缴获了大批物资。
第三支队的队长王明贵则盯上了克山县。这里地处平原地带,公路、铁路及电话网四通八达,是日军重点经营和派有重兵把守的要地。日军的顺口溜说:“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大东亚共荣圈,皇军不可战胜。”王明贵不信邪,就要在这里捅出个“窟窿”。
攻打克山的头一步,是要把敌军从克山城里调出来。8月份的时候,王明贵带着部队在北兴镇一带不断出击,每到一地,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然后,让老百姓去向日军报告。日军一开始不肯轻易出城,但他们听了多次报告,在城里呆不住了。
王明贵在9月中旬接到报告:从北兴镇到克山去的公路,都要经过屯子一侧,沿途高粱地挺多,比较好隐蔽。到了克山县城附近,地里长的都是矮棵的庄稼,只有离城七里多的地方,有一块高粱地可以隐蔽。眼下,日军强迫农民提前割地,企图尽快放倒青纱帐。
王明贵一听,当即决定: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21日,王明贵带着第三支队,刚从侯家屯出发,就听到哨兵大喊一声:“谁?”
对面回答说:“九支队!”接着,冯仲云和第九支队长边凤祥从对面走来。原来边凤祥支队就住在前屯,可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就在跟前。
冯仲云听王明贵汇报了攻打克山的计划,说:“我看就让九支队和你们一起行动吧。”
边凤祥说:“同意。”
王明贵说:“两个支队一起行动,那就由冯政委指挥吧!”
冯仲云说:“不行。我对情况不熟悉,还是由你来指挥。”
部队在24日夜间进入距克山县城七里多地的那片高粱地,挖好了工事。天快亮时,战士们躺在工事里睡了起来。
王明贵心情却挺紧张,附近的敌情使他难以入睡。紧靠高粱地东头的公路,日军的汽车和农民的大车来来往往,不时传来马达的轰鸣和马车夫的吆喝声、鞭子声。日伪军和来往的行人川流不息。附近的一块块地里,老百姓正在收割庄稼。西头有几个小猪倌在放猪,嘴里哼着小曲。部队正处在日伪军眼皮底下,一旦暴露,攻打克山县的计划就落空了,还会遭受大损失。他担心农民割地会把部队割出来,小猪倌进地找猪会把部队找出来……他通知各大队管理好武器防止走火,不准说话,不准离开工事,四周的哨兵发现猪进高粱地,立即慢慢轰出去,发现有人来就立即扣留。
谢天谢地,令王明贵提心吊胆的一天总算平平静静过去了。事先派进城里的侦察兵回来报告:“一切正常,情况没有什么变化。”
黄昏降临,部队换上伪军服装,打着伪军的旗帜,排成两纵队,大摇大摆向克山县城走去。进城后,王明贵支队和边凤祥支队分开,向各自的攻击目标奔去。
抗联队伍来得突然,城里的伪军根本没有准备。边凤祥支队攻打伪军团部,王明贵支队攻占伪县公署、打开监狱放出爱国群众,都没有遇到大麻烦。伪军一听是抗联队伍打进来了,大多数人不是举手投降就是撒腿跑了。只是王明贵支队攻打伪县公署大院后面的警察学校时遭到了抵抗,司务长中弹牺牲。参谋长王钧带人去没收银行,碰上了一个不知死活敢于抵抗的伪职员,还有顽固无比的金库。战士们打死了伪职员,却无论如何也砸不开保险柜,只好丢下它,从抽屉里翻出一些伪币带走了。
当克山城里打响以后,住在西大营的伪军几次试图进城增援,都被抗联阻击部队打了回去。西门外的日军凶得多,日本守备队队长带着全副武装的两汽车日军,拼着命往城里冲。他们在明处攻坚,抗联在暗处打援,他们连冲两次都失败了,只好撤走。
日军撤走了,王明贵达到了预期目的,并不恋战,下令撤出县城。这一仗,抗联牺牲一人,轻伤三人,战果累累:重创增援的日军,击毙一名日本警正,打死打伤二十多名伪警察,俘虏一百多名伪军,缴获四门迫击炮、一千多支步枪和几万发子弹,击毁三台日本军车,从监狱解放出三百多人,有一百多人参军。
攻克克山县城后不久,王明贵支队与边凤祥支队分开,准备西渡嫩江,开辟新的游击区。王明贵和王钧率领八十多骑奔赴大兴安岭山区,打响了著名的霍龙门战斗。
嫩江北部的霍龙门,是当时北黑线上的铁路总供应站。站内储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汽油、粮食和被服。
王明贵在战前进行了详细的敌情侦察。他和中队长修身,化装成赶大车的,赶到离霍龙门只有十多公里的炭窑,走进炭窑窝棚,只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正忙着做饭。他们向老人说明了真实身份和来意,要求他协助侦察敌情。老人说:“为了抗日救国打日本,有啥需要我办的就尽快说吧,咱没说的!”
老人说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霍龙门的日本兵营,常驻兵力很少,每天从嫩江站开来一列车日军,有时住下,有时返回。
王明贵请老人带修身去霍龙门车站侦察敌情。老人说:“最好我一个人去侦察,免得引起敌人怀疑或出现意外。”最后约定,当晚到炭窑窝棚听消息。
天黑时,老人回来了。他亲眼看见了三四百名日军上了开往嫩江县的火车,就赶紧回来报告。
10月17日晚,部队接近了霍龙门,在一个山脚下停住。各大队按战前部署,由炭窑工人带路,分头奔向进攻目标。
徐宝和率领第八大队最先到达伪军骑兵连营房。伪军哨兵向冲锋队开枪,成了抗联部队发起全面冲锋的号角。冲锋队员手持早已准备好的两条毛毯,往铁丝网上一搭,后边的战士紧跟着冲入院内。伪军骑兵连的官兵躺在炕上就成了俘虏。
经过九十分钟战斗,王明贵支队缴了伪军的枪,打死打伤六名日军,俘虏了二十多名日本工程技术人员。日军的铁路供应总站,变成了王明贵支队的物资补给站。每个战士装备了两匹战马、全新的军大衣、棉衣、皮鞋、皮帽、皮手套和两条毛毯。他们将分给群众以后剩下无法带走的物资付之一炬,使霍龙门变成了“火龙门”。
1939年秋天,日军严重破坏了松花江下游的抗日游击区,又将进攻矛头指向东南满地区的抗联第一路军。关东军成立了“联合讨伐”司令部,集中了日伪军警宪特共七千五百多人,大规模进攻抗联部队。日军把杨靖宇视为眼中钉,成立了四支“专对杨靖宇的部队”。
为了抓住杨靖宇,这些部队个个使出了看家的本事。他们先是按区域在飞机配合下,采取“陆空呼应”、“踩踏战法”,进行联合“围剿”,继而打破区域界限,只要一发现杨靖宇的部队,便穷追不舍,以所谓“狗蝇子战术”死死叮住,越区追赶。
日伪军的这些损招,使杨靖宇的部队陷入了困境。
杨靖宇在1940年初率部回到蒙江县。为了筹集给养,袭击了日军的重要据点龙泉镇。这次袭击取得了战果,但暴露了行踪。日伪调来大部队,在蒙江境内到处张罗布网,决心一举消灭杨靖宇。
杨靖宇的部队改变集中兵力夺取衣食的计划,化整为零,采取了一系列迷惑敌军的措施,日伪军一时无法确定杨靖宇的准确去向。
1月21日,部队在蒙江县马家东南方密林地区与日军“讨伐队”作战,警卫旅第一团参谋丁守龙负伤被俘,然后叛变。他是知道杨靖宇行踪的。
日军按照丁守龙提供的情报,一次又一次把搜捕的大网准确地撒到杨靖宇所在的小部队头上。杨靖宇带着小部队左突右冲,总是冲不出包围圈。这时候,部队里又有一个张秀凤叛变。杨靖宇带着十五名战士,被张秀凤带走七个,只剩下七名,一个脚肿,一个有病。
日伪军对这几名抗联军人紧紧追杀,杨靖宇身边只剩下两人,被日军封锁在伐木场附近的山中。三名军人面临着饿死的危险,两个警卫员冒险下山买粮,牺牲在日军枪口下。日军从他们的遗体上搜到杨靖宇的印章,估计他就在附近山上,于是加紧封锁各条道路。
杨靖宇孤独地熬过了饥寒交迫的五天。为了生存和战斗,他孤身下山买粮,走到三道崴子路边,碰到几个打柴人,便请他们代买粮食和棉鞋。这几人中,有一个是伪满的牌长,回到村里就向日军告密。“讨伐”队迅速开到,将筋疲力尽的杨靖宇包围在一片小树林里。日军逐步逼近到五十米处,喊话劝降。杨靖宇一声不吭,双枪射击,连续打倒五名日军,“讨伐”队一死四伤。日军知道已经没有指望活捉杨靖宇,就猛烈开火,杨靖宇左腕中弹,手枪落地,右手的驳壳枪还在射击。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胸部,他倒在地上,壮烈牺牲。
日军估算,杨靖宇饥饿已有半个月,完全断粮至少在五天以上,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山林,没有房屋可以御寒,坚持活下来了,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将杨靖宇的遗体送到县医院解剖,切开肠胃,看到的只是草根和棉絮。在场的中国护士禁不住流下热泪,日本军官则狠狠地说:“算他是支那的一条好汉!”
日本关东军将杨靖宇的头颅切下,送到伪满的“新京”长春保存,同时在杨靖宇殉难处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将遗体下葬,以这位中国将领的顽强为榜样,训戒自己的部属。
长春解放后,泡在药液中的英雄头颅被找到,脸上冻伤的痕迹还清晰可见。人们用他的头颅制作了塑像的印模,然后将头颅与躯体合葬在通化烈士陵园。
杨靖宇牺牲后,抗联第一路军的重担全落到魏拯民身上。但是,久病的魏拯民已经难以胜任率军到处转战的重任。中共党组织决定,把他送到吉林省桦甸县夹皮沟的牡丹岭密营养病。
密营的生活极其艰苦。秋天,日伪“讨伐”最为频繁。密营里古木参天,浓林密布,不见天日,遇上下雨天,找不到一块干燥的地方,没过多久,魏拯民就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
入冬后,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多度,他们却不敢生火取暖,只要一生火,日军飞机就会发现地面冒出的烟,便会出动部队或用大炮轰击。
密营里,人们还受到饥饿的威胁。他们不得不经常冒险去打猎。魏拯民的警卫员黄正爱,在与黑熊搏斗时牺牲。1941年3月8日黎明前,魏拯民从昏迷中醒来,吃力地把一包文件交给身边的通讯员,再三叮嘱他一定要交给党组织,转给党中央,然后停止了呼吸。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