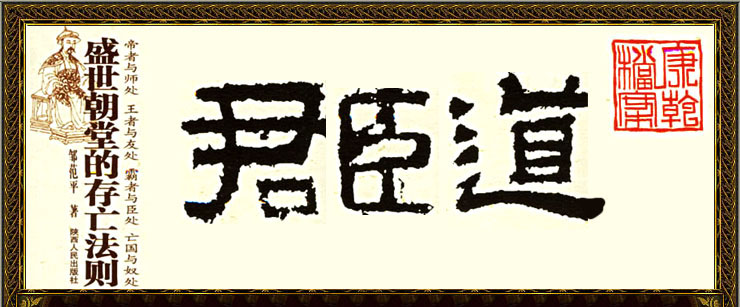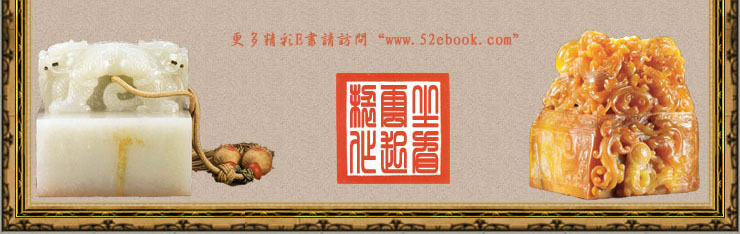雍正元年九月,云贵总督高其倬上疏反映情况,说: “云贵两省土司承袭一事,向来有向地方衙门送礼的陋规,上下衙门,每每因为文书中有错字,借故刁难土司,意在索取陋规。臣已严行禁革,并请求今后上报六部的文册中,若有个别几个错字,无关大局者,免予驳换。臣于疏内代为声明,以便土司承袭一事易于了结。”高其倬的奏疏正符合雍正帝整顿吏治的精神,所以立即得到雍正帝的嘉奖。可是高其倬为人圆滑,不大肯弹劾官员。当时有一位以弹劾官员而得到皇帝赏识的封疆大吏,就是田文镜。
田文镜(1662~1745),清汉军正蓝旗人,后因受雍正帝宠爱,被转入上三旗之正黄旗,田文镜仅是监生出身,历任县丞、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田文镜祭华山经过山西,见到山西正闹饥荒,百姓大量流亡,而巡抚不闻不问,也不上报朝廷。他返京后,把山西的情况如实汇报皇上,雍正帝十分欣赏他的坦率直言,命他前往山西赈灾,拯救了七八十万灾民。事后,他授任山西布政使,并不断提升,他由一个八品小吏快速升至一品大员,完全靠的自己的才干和勇气,当然也是因为遇上了雍正帝。他由河南布政使而巡抚而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雍正帝又置河南、山东总督,由田文镜任之。
雍正帝用人惟贤,或因事权授,往往不拘定制。督抚的设置时有变化。比如,直隶原设巡抚,为李维钧改作总督,后成为定制。闽浙总督先为一人,雍正帝用李卫为浙江总督,兼理江南五府二州的盗案,于是福建也单独为一总督。鄂尔泰改土归流时期,两广总督辖下的广西割归云贵总督。巡抚,历来各省只有一个,当王国栋署理山东巡抚时,雍正帝又用吏部左侍郎刘于义协办山东巡抚事务。伊都立为山西巡抚等等。这是雍正帝用人行政敢于打破成规的表现。
田文镜在河南厉行廉政,毫不瞻顾,不避嫌怨,弹劾贪官污吏数十人,他因此屡遭攻击和贬抑。从朝廷大员到下辖官民,反对他的人非常之多。陕西延安知府沈廷正原系雍王府旧人,颇不满意田文镜。雍正二年,他调任河南开归道,田文镜因他是雍王府旧人,有所顾虑。雍正帝在田文镜的奏折上批道: “听说他未到河南即先存成见,欲与你作梗。试想朕岂有命一属员前来约束上司,使之掣肘于你之理?他要是露有不肯尽心协助,实力承办,反而倚仗其雍府旧人身份,借端生事,妄作威福,出卖你而取媚于他人的情景,你可严加参劾,待朕重惩,决不姑息,你接到此谕可与他共观之。”
当时,雍正帝常常以在一位官员的奏折上批示,同时令其他官员知悉的方式发布上谕。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使官员互相监督。有人认为,田文镜所以提升极快,因为是雍王府旧人,所以格外受到重用。其实田文镜并非雍王府旧人。雍正帝既然做了皇帝,再偏袒雍王府旧人就太狭隘了,对沈廷正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
得到皇帝支持的田文镜,在河南以极严厉的手段大刀阔斧地整刷吏治,剔除陋规。整顿吏治成效不大的原因之一,在于上下不同步进行,往往是对下严而对上宽。约束下属官员容易,抗拒上峰则难。有一次,钦差大臣何国宗到河南办公,按照通常的规矩,地方官要送礼给钦差大臣。田文镜的左右对他说,您对下面可以严禁陋规,对上面却不可不敷衍一下。他却说,岂有对下严而对上宽之理?欲禁州县之火耗,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除陋规。他坚决不送规礼。何钦差没有得到红包,认为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回京后就到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可是皇帝反倒因此更加器重田文镜。因为他的行政风格,恰恰体现了雍正帝振刷数百年颓风的革新精神和政策,雍正帝对他雷厉风行施行严政的手段十分欣赏,特为他设河南山东总督一职,并把他树立为“模范疆吏”。所谓“数百年颓风”是把明朝也算在内,在明朝初期,朱元璋曾经下大力气肃清贪污,以后就没有皇帝再大力整治贪污了。清朝,康熙帝大力提倡清廉,对于贪污的官吏有时虽然也严厉打击,但更多的是以规劝的方式教育,效果不太好。康熙帝晚年吏治松弛,以至于国库都空虚了。雍正帝眼里不揉沙子的性格决定他行事的坚决果断,打击贪官污吏绝不手软。
田文镜对治下的贪官污吏,毫不徇情,坚决题参革职审查,三年之内,他共参奏属员22人。雍正帝赞许说: “田文镜参官最多,鄂尔泰从不轻弹,然二人皆各有道。”鄂尔泰的事情,后面再说,这里只说田文镜参奏隆科多一案,颇有些戏剧性。有一天,他的师爷邬先生问他: “公愿为名巡抚呢,还是做普通巡抚?”
田文镜说: “谁不愿意做名巡抚,庸庸碌碌有什么意思?”
邬师爷说: “公若愿为名巡抚,须任我草一疏上奏,但疏中一字不能令公看,可以吗?”
田文镜平时上的奏折,凡是由邬先生代书的,往往得到皇帝嘉许,所以对他极为信任,于是同意了。邬先生的奏折由田文镜盖印发出。奏章发出去以后,邬师爷才告诉他,是弹劾国舅隆科多贪污受贿等罪行的奏章。田文镜听罢,连连叫苦,生怕因此惹出大祸来。
邬师爷却笑着说: “皇上早欲除去此人,不过苦于没有借口而已,公无须顾虑。”
果然,皇帝将田文镜的奏折交部臣议处,结果,隆科多被罚为永远监禁。朝野上下都佩服田文镜有胆量。
以后田文镜又对邬师爷的孤傲性格有些厌烦,邬师爷便辞职不干了,田文镜的奏章就常常受到皇帝的申斥,田文镜只好再把邬师爷请回来。有一次,雍正帝还特意在批复奏章中问候邬师爷。于是田文镜再也不敢轻视邬师爷了。田文镜死后,许多封疆大吏争相以高薪聘请邬师爷,邬师爷一概拒绝。传说,后来邬师爷到了京城,有人还在宫中见过他,因此怀疑他是雍正帝派在田文镜身边的人。这也并非不可能,封建政治黑暗的一面,怎样估计都不算过分。
言归正传,犁剔陋规可要比弹劾某一位高官困难得多,因为它是全体官吏的命脉所系,所谓“千里做官只为钱”。陋规也是官场腐败的一面镜子,官僚体制的运转的主要动力就是陋规,所以骂田文镜的人特多。
田文镜也深知自己的处境,就任河(南、山)东总督之际,他上奏折说: “臣在河南行政,使贪官墨吏、玩法士民不得遂其私,多称不便。因此谤腾毁积,物议风生。臣到山东仍照河南一样行政,山东也会怨声蜂起。臣一如既往,不恤人言,坚决把河南的政策移到山东,以不负皇帝之宠眷。”田文镜在山东总督任上,一口气剔除官衙陋规数十项之多。
田文镜为犁剔山东粮驿道衙门的陋规,直接向雍正帝奏报户部等中央衙门接收陋规的情况,请求禁止。廉政要想实际有效,必须上峰不收规礼才行,否则地方也难于实行廉政。一时,从地方到中央,怨声蜂起,田文镜屡遭弹劾,但是雍正帝却十分信任他,支持他。陋规是官场痼疾,既然是下级向上级送礼,只整顿地方,不整顿中央,本末倒置,起不了作用。整顿下级,叫下级不送,何如整顿上级,叫上级不勒索?田文镜反腐败搞到中央六部,能不遭人忌恨?田文镜铁了心就是不怕,因此很得雍正帝的青睐。
高其倬、田文镜奏请革除这一弊政得到了雍正帝的坚决支持,却得罪了中央大员。因为京官没有机会直接搜刮百姓,必然要吃外官。而外官只要有事报批,就只好被吃,送礼不断。“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乡同年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敬。”通常是在夏至之前或冬至之以后不久,派专人持“问安函”附“敬费”奉赠京官。至于具体的钱数,也有一定之规。以“别敬”为例,外调的官职较高或所任是肥缺,送钱就多一些,反之就少一些。比如雍正初年西北用兵之时,陕西粮道就是肥缺,“别敬”要送17000余两左右。当然不是只送给某一人,也不是大小官吏平分,其中也要分三六九等。关键人物得大头,次要人物得小头,一般的人物沾点光而已。如果光赠大员,不送小吏,他们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让事情办不好,起码要拖延几天,“懂事的人”不能不按陋规办事。
下面说几个关于陋规的故事:
康熙五十一年,方苞因文字狱“《南山集》案”入狱,出狱后有《狱中杂记》一文,讲述狱中陋规。狱吏与狱卒向犯人收取陋规心狠手辣: 死刑犯也要交陋规,交了就死个痛快,否则就尽量延长你受痛苦的时间。有人被判凌迟,交规钱者,先被刺心,不交者,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痛苦可想而知了;绞刑则反复数次才使人断气;捆绑犯人也是如此,不交钱就把臂膀捆伤,终身残疾。方苞问: “与被刑、缚的人,又没有仇,实在无钱,何不稍稍放宽一些,岂不是仁术吗?”老吏说: “这是为了立规矩,以警示后人。不如此,他们就会存侥幸之心。”
雍正十年(1732年),发生了一件借命索规的惨剧,说来令人发指: 河南学政俞鸿图被人弹劾,告他贿卖秀才,赃私累万,雍正帝大怒,下令将俞鸿图立即革职,严加审训。半年后,判处斩立决。处决犯人,也是刽子手向犯人索取陋规的极好机会。如果收受了规费,就可以一刀落下,立时毙命,犯人死个痛快。不得规费,则“刀下留情”,使犯人想死也死不了,痛苦至极。俞鸿图忽然被押赴刑场,他事先毫无准备,来不及向刽子手送规费,他被斩为两段,上身在地上乱滚,奄奄一息而不死,他以手沾着自己身上的鲜血,在地上连续书写七个“惨”字,其宛转未死之状,令人目不忍睹。事后监斩官据实奏陈,雍正帝也为之恻然,于是下令封刀,从此废除腰斩之刑。
上司利用权力勒索下级,收取陋规,已是代代相因的公开的积弊。总体来说,清朝皇帝比起明朝的皇帝要精明得多,他们都十分清楚其中的奥妙。早在康熙朝,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就曾向康熙帝上密折,反映地方官收取陋规情况,请求禁止。康熙帝批示道: “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目前之计,恐怕以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又有一次,曹寅反映,前恩准借给两淮盐商库银100万两,但是商人实收只有80万两,对此康熙帝只有三个字的批示: “知道了。”曹寅向康熙帝奏请革禁两淮盐课浮费所列出的院费、省费、司费和杂费四大项陋规,其中送给江苏省督、抚、司、道各衙门的规礼就有三万四千五百两。康熙帝对此批示道: “此一款去不得,去则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皇帝难道还不敢得罪于督抚吗?康熙帝是怕督抚因捞不到油水而不肯尽心做事,或再向小民加收火耗,因此对官场的陋规总是采取容忍的态度。由上述几例可见: 社会生活中,陋规之多,其无孔不入,简直就像空气和饮水一样。
各地的大小官吏们贪得无厌,他们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分享贪赃。州县官吏把赃款的一部分据为己有,一部分以种种名义馈送上司。正如康熙朝林启龙在《严贪吏以肃官方疏》中所说: “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以州县之大小,分礼物之多寡,以馈赠之厚薄,定官评之贤否。”康熙帝对陋规深有了解,他曾说: “地方官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可是,他对贪官污吏的处理却相当宽大。以至官场中陋规累累,贪污冒领,相习成风。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川陕总督岳钟琪在一份奏折中,详细开列了两省五花八门的各种杂派项目,较大的有三十多项,他说: “以上所开陋弊,有包差、定差、轮差、飞差种种名色。在各州县原非尽同,或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或更随事生法,自难搜罗枚举。至于派敛银数,又各随州县之大小,其间多寡迥别,且派一分,则百姓所出必不止一分,以吏役头人层层侵剥,官府明知其弊而不能查,故民间派银数目难以核实。”
雍正帝批道: “此奏甚属公诚,不但川陕,各省皆然。”雍正帝对官吏收受陋规一事的态度不同于乃父,他决心以雷厉风行之势,大力整顿吏治,肃清贪污。田文镜正是他在地方上的得力大员。雍正帝执法严峻,田文镜严刻的行政风格与其十分相似,所以很受他器重。他坚决支持田文镜犁剔陋规的举动。雍正元年,雍正帝发布谕旨说: “各省奏销钱粮,积弊甚大……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本内数字互异,或钱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而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可准予奏销,或仅将无关紧要之处驳回,以存驳诘之名,掩饰耳目,下次覆报时,即予议准。官员内外勾通,欺盗虚冒……朕今不得不加以整理。”
山东蒲台县知县朱成元在任期间,凡给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等官员送陋规,都予登记。被人揭发出来,田文镜对朱成元和受礼的前巡抚黄炳和博尔多、余典等人进行审讯,严厉整饬。
雍正帝大力支持田文镜搞政治革新,夸他是“巡抚中第一人,若各省督抚皆能如田文镜、鄂尔泰则天下大治矣”。
田文镜得到雍正帝的赏识有秘诀。有人说: “世宗生性高傲,好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臣下奏章,虽然殚精竭虑,却故意留下一两处罅误,以待批驳,或故作一二误字,以待改正。非如是则世宗之心必不快,将格外吹索,而前程危矣。田端肃文镜深知其妙,对豫省民则苛刻搜求,务以严厉为尚,对朝廷则强作呆态,似不解事,故官河南、山东总督最久,帝眷最宠……”(柴蕚《梵天庐丛录》卷二)简单说来,就是对下精明,对上装傻。田文镜奏折表示: “臣目中惟知有皇上,君臣大义如父子天性,间不容发。”“总之此心惟知有君,则凡是悉秉至公,无人不可以共事。”这就是“强作呆态”,雍正帝批道: “难为你此数句议论。”(《雍正奏折》六、七田文镜)雍正帝的精明原来如此。
田文镜死后,雍正帝这样评价田文镜: “老成历练,才学兼优,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