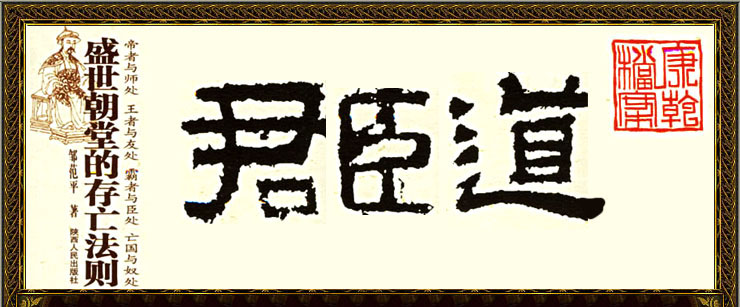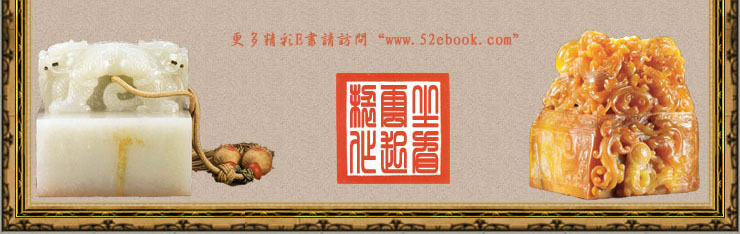许多人都认为,史书是被人随意编造的,或是被人打扮的小姑娘,或是下跪的婢女,等等。满臣都自称奴才,满清的史书当然就是奴书,因为它不是本来面目。
乾隆帝乾隆帝即位时正是权欲旺盛的青春期。顺治帝六岁即位、康熙帝八岁即位,此时他们都不会对权力产生巨大的欲望。童年皇帝即位后不可避免地需要有一段摄政王辅政时期,康熙和顺治都是如此。相权的作用因此非常突出,这是无可否认的,然而因此也就留下了后遗症。虽然雍正帝即位时已经成年,但是,康熙帝晚年长达十年的储位之争,却使得雍正帝即位必须由大臣传达遗诏,来为自己登基的合法性作证明。隆科多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隆科多的命运也就很不妙了。一般人们都从以下两个方面看此问题: 一、雍正帝杀人灭口;二、隆科多是权臣,为皇帝所不容。其实还有一个因素被人们忽略了,就是新皇帝往往不原意承认这样的事实: 在大行皇帝驾崩之后,新君登基之前,有一段最高权力的空缺期。此时,宰相大臣的作用就是关键性的。对此,雄才大略的皇帝必然会感觉很不舒服,这是隐形的君臣矛盾,不被人们注意。甚至会以为笔者在无中生有地制造君臣矛盾。虽然本书非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论从史出”的原则也是不可违背的。乾隆帝这位自视甚高的人主,“君为臣纲”的思想在此事上就表现得非常典型。
按照张廷玉自订年谱,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清世宗实录》的记载,宣布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的谕旨是在二十三日子时之前,当时雍正帝尚未去世,那么,君权的授受就是在父皇和储君之间进行。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密旨的公布是在雍正帝去世之后。
雍正帝密诏除藏于乾清宫之外,另书内容相同的传位诏置放在圆明园内。八年九月,雍正帝重病,他将此事秘密告诉张廷玉,及至鄂尔泰内召,雍正帝又于十年正月向鄂尔泰、张廷玉做了说明,并说“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雍正帝常常居住圆明园,故在大内诏书之外,又备书诏一份,为防不虞。雍正帝死后,弘历以痛哭流涕表现孝道之时,张廷玉、鄂尔泰乃向允禄、允礼等人表示: 如今正大统是急事,大行皇帝曾示我二人有密旨,外此无有知者,此旨收藏宫中,应急请出,以正大统。
几位大臣同意,问总管太监却并不知有此密旨,更不知藏于何处。张廷玉说: “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旨。”据之寻出,打开一看,正是传位弘历密旨。由张廷玉就灯下宣读,众臣拜请弘历受命。弘历随即令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如此安排之后,就扶雍正帝榇舆返回大内了。(《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三)同时“捧遗诏从圆明园入禁城”。(《鄂尔泰行略》)可见不是从人们所熟知的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取出的。新君即位一事,大臣们尤其是张廷玉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突出。
《清高宗实录》却将此事加以改造,说成是雍正帝子时死,弘历于寅刻至大内。地点和时间就不对了,提前了一个时辰,地点由圆明园改在紫禁城。内侍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雍正元年所封诏书,等候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到齐,然后启封,才知道嗣君之事。最高权力的交接就不必依赖大臣执行大行皇帝的遗命,而是皇太子宝亲王在即位以前就颁布了一道谕旨: 着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这表明,在雍正帝病危不能行使权力的情况下,皇太子已经代行君权,君臣名分已然确定。这里只字不提圆明园诏书,显然是为了抹煞鄂尔泰、张廷玉在权力交接中的作用。弘历说他在雍正八年六月亲奉乃父谕旨,谓“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当初,张廷玉修实录,将许多不利于雍正帝的事实删削,现在《清高宗实录》又是如此办理。连不必篡改的事情也篡改了。我们怎么能轻易相信史书呢?所以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袁枚所撰写的《鄂尔泰行略》,比张廷玉的年谱还要突出宰相的作用,把鄂尔泰视为顾命大臣: “捧遗诏从圆明园入禁城,深夜无马,骑煤骡而奔,今上登极”。乾隆帝不原意承认在雍正帝去世与自己遵旨即位之前有一个由宰相鄂尔泰、张廷玉来填补的最高权力的空缺期。真实的历史总是不堪承认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尽管它是非常短暂的,乾隆帝却领会到,此事对君权具有深刻的否定意义。由鄂尔泰、张廷玉宣布立储遗旨,确立弘历的继承人地位,对于乾隆帝是一个羞辱。事后他必然要以某种方式整治这两位使他蒙羞的宰相。
在最高权力更迭中,尽管这个由大臣填补的空缺极其短暂,但对于皇权也是一种威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