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杂谈《读书杂谈》
作者:钱理群
一、“随便谈谈”

鲁迅在演说一开始,就点明自己是来“随便谈谈读书”。这大概有两层意思。首先是并无特别的设计,也无深意,不过是“忽而想到”就“随便谈谈”。下面谈到读书时,鲁迅也说要抱“随随便便”的态度,不要一本正经地摆出一个读书的样子:“我在读书了!”鲁迅还有一篇文章,也是谈读书的,题目就叫《随便翻翻》,这都是在强调,无论演说,还是读书,都不要端架子,要自自然然地,兴之所至地讲和读。其次,还要强调,因为是“随便谈谈”,所以讲的都是“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就是说,不是来作“指导”,也不是来作“指示”,而是发表一己之见,不过是“姑且”讲之,听众也就不妨“姑且”听之。
这样讲,不仅是为了缩短和听众的距离,更是一种演说者的自我定位,这就是鲁迅在另一篇演说《关于知识阶级》里所说的:“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鲁迅一再说,自己绝不是“导师”,当然更不是“国师”,道理也很简单:自己并不掌握真理,只是一个探索者,连路都不知道该怎么走,如何给别人(包括中学生听众)指路?他因此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告诫年轻人,千万不要轻信那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过能说话”,“不过能弄笔”,“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要他们当导师,是绝对不可以的,甚至是有害、危险的(《导师》)。
二、“杂谈”与漫说
“随便谈谈”不仅是一种演说的姿态,也决定了演说的内容、方式、结构:“杂谈”与漫说。不仅“杂”,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而且“漫”,东拉西扯,漫无边际。忽而“职业的读书,嗜好的读书”,忽而“文章和文学”的区别,忽而“弄文学,看什么书”,忽而“如何看待批评”,忽而“读世间这一本大书”:就这么不断地转换着话题。在具体展开时,就更是随意举证,枝蔓旁出。又是“木匠磨斧头”,又是赌徒“打牌”;又是“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又是“到广东吃荔枝”;又是创作家脑子“发热”,又是教授摆“架子”,等等,等等。真可谓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思想无羁地漫游,话语也随意地流动,整篇演说,舒展、从容,有一种说不出的自由感。
但却又是“杂”而不乱,“漫”而有序,放得开,收得拢。从总体而言,无论话题拉得多开,也始终不离“读书”这个中心。可能是考虑到听众多为中学生,因此,在结构上,也作了一些条理化处理。例如,在谈到自己对文学的看法时,就明确列为三点。文章结尾处,也用“总之”一语把演说的宗旨作了明确的概括:一是提倡“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二是强调“和现实社会的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这也是演说的中心和重心所在,是我们在读与教中应紧紧把握的。
三、“别人说不出的话”
鲁迅曾说过,他或许能够说出一些“别人说不出的话”。同样是“随便谈谈”,鲁迅谈起来,就会别开生面,给听众以意外的启发和惊喜。
前面提到的文章的那两个主要观点,就很有见地,我们八十年后听起来也仍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他在展开论述中,更是处处显出思想的锋芒。不妨举几个例子。
比如,“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千百年来,人们总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今天,应试教育这么盛行,也是因为应试可以致仕(升官发财),也自然以读书为高。这背后其实还隐含着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比木匠、裁缝(普通劳动者)高尚的理念。现在,鲁迅将“读书”与“磨斧头”、“理针线”,将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置于同样地位,这自然是对传统和世俗的读书观的一个挑战。
还有,“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是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读到这一段话,人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学理工的瞧不起学文科的,做学问的人瞧不起经商、当官的,或者反过来,重文轻理,重管商而轻治学教书,等等,人们见怪不怪,鲁迅却偏要质疑,而且还挖掘出其根子:这背后,有一个将知识与职业划分等级的观念,实际是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级化。这自然还会涉及社会体制的问题。这样的开掘,自会引出更深的思考。
再看这一句:“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这里所谈已不只是批评家的问题,而触及到“文坛”(思想文化界)中占据“最高位”,也即权力的掌握者,同时拥有了创作的“生杀之权”的问题:这正是对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揭露。“灵魂上挂了刀”也就成了一切实行文化专制的“精神刽子手”的一个写照。
这就谈到了鲁迅演说中的现实针对性。他经常“附带”说到现实中的某个问题,点到即是,并不展开;如果不了解演说的时代背景,就很可能忽略过去。比如这一句:“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说是“附带”,其实是特意说的,因为正是演说前三个月,即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大屠杀,演说的前一天7月15日武汉政府也开始了大屠杀,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抓捕、枪杀,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亲俄”,是所谓“赤色份子”。显然,鲁迅正是要通过这“附带”一句,旁敲侧击地对国民党的屠杀提出他的抗议,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这样说是需要勇气的。我们也因此懂得了他这篇演说的深意:反复告诫青年不要“躲进研究室”,“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正是暗示和提醒听众要敢于正视现实的黑暗和血腥,不要逃避。这些话,真的是别人说不出的。
记得老舍说过,鲁迅的语言“永远软中透硬”。我们前面说,鲁迅这篇“随便谈谈”,自有一种舒缓而从容的风致;现在,我们又感受了其内蕴着的批判锋芒。他的演说的魅力正体现在这软、硬两面的张力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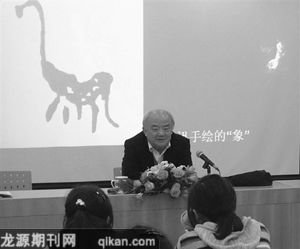
四、“很普通的比喻”及其他
老舍对鲁迅的语言特点,还有一个概括:“他会把最简单的言语(中国话)调动得(极难调动)跌宕多姿,永远新鲜,永远清晰”。
本篇因为是演说词,而且听众是中学生,就更要求通俗、明白、清晰,但又必须吸引人,做到“多姿”而“新鲜”。
鲁迅告诉我们,他的秘诀是多用“很普通的比喻”。前面提到的“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还有“游公园”,到广东“吃荔枝”,这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取喻,既来自听众熟悉的身边人和事,自然通俗易懂,但又赋予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以另一种意义,自然就构成了一个新鲜的发现。
当然,最为叫绝的,还是“打牌”的比喻。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鲁迅的一个“神来之笔”。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他是在讲完了“读书”并不是特别“高尚的事情”这个意思以后,突发异想,就把“读书”的“嗜好”和“打牌”的“嗜好”联系起来,发了一通妙论:“读书”要和“真打牌”一样,“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即“离开了利害关系”,只为“在(书的)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本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读书”和“打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并且似乎是处在“高雅”和“低俗”的两极,因此,这样的联想实属“荒谬的联想”。但鲁迅却巧妙地发现了其中的联结点:都是一种“嗜好”,都充满了“趣味”,而且都是“自愿”的。这样的妙语牵连,不仅让人喜出望外而眼睛一亮,更含有打破“读书高尚、神圣”的迷信的作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