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蒋锡夔:寂寞长跑
作者:佚名
2002年,蒋锡夔院士带领的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课题组,以一项名为“物理有机化学前沿领域两个重要方面——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的研究”,获得了连续多年空缺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摘得了中国基础科研的这一桂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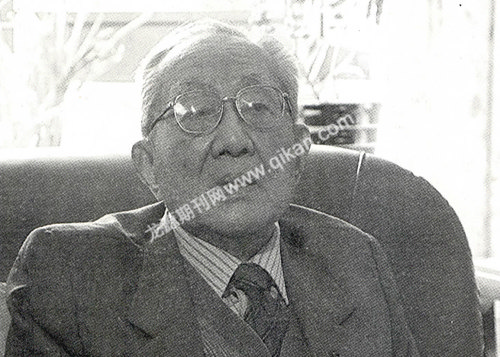
我从来就没有感觉寂寞过
蒋锡夔院士在2002年度获得中国基础科研的这一最高荣誉,可以说是为所有科技界人士争回了面子。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世界一流成果的背后是蒋锡夔在实验设备简陋、经费极其紧张的条件下,前后带领54人默默工作了20年。因此在他们获奖之后,许多媒体都用 “寂寞长跑”来形容他们走过的这20年。
蒋锡夔:我曾经看见报上说我们很寂寞,可我觉得享受寂寞也是一种快乐,我对化学实验永远感到非常有兴趣。我的想法很简单,都是关于实验结果的,要么结果是正面的,要么是反面的。如果是反面的,我马上换个小方向,或者大方向,改变我的目标,所以不感到有什么寂寞的。相反,等到把你的想法做出一个真正新的反应条件,那将是非常高兴的。
记者:因为您的爱好都在里面,自然不会觉得寂寞。
蒋锡夔:对,就是这样。
在国际上,除应用科学外,衡量一个国家的科研水平更多是看其基础科学研究,诺贝尔奖的评审就是如此。蒋锡夔选择这个课题时,国际上并没有系统的研究方法,对于该领域能深入到什么程度也无人知晓。但可以确信的是,虽然在短期内无法看到其实用价值,但一旦做出结果,将会对人类科学产生深刻的影响。
记者:比较而言,能在基础研究中做出一些成就是不是更重要,也更不容易?
蒋锡夔:对我来说,不存在重要不重要的问题,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是我的家庭特色
蒋锡夔1926年9月生于上海,家境富裕。他的父亲蒋国榜是杭州的富商,人称“蒋半城”。“杭州的花巷观鱼,有名吧,解放前都是蒋家的!”蒋锡夔的同事们介绍蒋锡夔时这么说。
不过,他父亲虽然继承了大量的家业,但对做生意毫无兴趣,毕生寄情山水,酷爱诗文,交往的朋友也都是社会上的文人雅士。母亲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知书达礼,温文尔雅。父母宽厚仁慈的品德对儿时的蒋锡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记者:您父母都不像商人,更像典型的文化人。
蒋锡夔:我父亲看得起的朋友都是文人画家,他最瞧不起做生意的人。这个当然是不对的。我是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这个很普通;但是我父母在资产阶级里是特别好、特别讲道德的一些人,这是我的家庭特色,可以说是从小到大影响我灵魂的。我父母继承了传统中国文化的道德观念,对此我也是深信不疑的。我始终认为,我们现在对儿童的教育,没有强调真正的“德”字。
当时我父母跟我讲的都是孔老夫子的道德标准。他们教我为人要诚实,不要追求名利,要追求真理。我想现在我们对小孩子的教育走歪路了。我知道我一些朋友的孩子,进小学不久马上就想当干部,没选上还哭一场。你教孩子的时候,就不要强调选小组长、小干部什么的,让他们懂得比如说在公共汽车上给老人和病人让座,这就是很好的道德教育。
far far away ,there is my star
(在遥远的天边,有一颗属于我的星星)
在父母的熏陶下,蒋锡夔从小爱好广泛,不仅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而且还爱听音乐、喜爱文学。
从16岁起蒋锡夔开始写日记,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几乎从未间断过。一本本已经发黄的日记本,记录着蒋锡夔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成熟科学家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历程:
“吾将往大学报名,余已定读化学,余之一部分为振兴中国工业农业,读化学当未出轨也。”——1943年8月20日
这一年,蒋锡夔17岁,不久他顺利地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如果说,父母的言传身教塑造了蒋锡夔善良正直的品格,那么在大学一年级发生的一件事,则让他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蒋锡夔:我年轻时候是很害羞、很内向的,当时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后来很快就断了,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的理想,我觉得在那个年纪谈情说爱不合适。
记 者:那时候您多大?
蒋锡夔:大学一年级。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人生了,人生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当时不是谈爱情的年纪,而是追求真理、追求真善美的年纪。
记者:那当时您喜欢那个姑娘吗?
蒋锡夔:还是相当喜欢的。但是我觉得自己太年轻了,想做很多事情,追求真善美,而谈恋爱跟这些都矛盾起来了。我看书的时间都不够,还参加了学生运动,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去恋爱,所以我就把它断了。
人生的追求是什么?理想又是什么呢?年轻的蒋锡夔在不断的自我拷问中,明确和完善着自己对人生的思考:
“我的生命将向着一个方向走:快乐,真善美的追求。我不要再落在这充满着各种滋味的人生轮回里。”——1944年5月20日
蒋锡夔最爱听德沃夏克作曲的《自新大陆交响曲》,在经历了感情的洗礼、确立了人生的目标之后,他用青春的激情为这首曲子写了一段歌词。
记者: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这个音乐呢?
蒋锡夔:它这个主题特别美。
记者:您给它改编了一段歌词?您现在还记得、会唱吗?
蒋锡夔:我不会唱了,我只记得前面两句了:far far away, there is my star.
记者:翻译过来是:“在遥远的天边,有一颗属于我的星星”,它是我的理想,它永远照着我的命运?
蒋锡夔:就是这样。
记者:那时候您已经有了自己的理想了?是什么呢?
蒋锡夔:就是追求真善美。 真善美的思想对我来说,来自自然。
在树立了“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理想之后,蒋锡夔将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专业学习中。1947年,蒋锡夔获得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特等荣誉理学士学位,第二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2年,他在美国凯劳格公司从事科研工作,其间发现了一种有用的有机反应,从而合成了一种新的氟化合物。1955年,在海外留学多年的蒋锡夔毅然决定回国参加建设。
记者:我听说您决定回来的时候,美国的移民局还专门派了两个官员跟您谈话?
蒋锡夔:是这样的。我在拿到学位后就提出来,我要回国。他们不许我回来。后来我在那个凯劳格公司做研究员,他们跟我谈话。他们问,你要申请回国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你是不是没有一个漂亮的姑娘给你做妻子,我们给你物色一个,证件什么的我们给她办,你只要同意留在这儿,留在美国。
记者:后来您是怎样回答这两个移民局官员的呢?
蒋锡夔:我说,我对美国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做人最讲究的就是信用,我来美国之前就立下两个志愿:第一我只为中国人服务;第二我要回来照顾我父亲、母亲,这就是我的诺言,有了这个诺言我必须要执行,这是我的道德的根本。所以不管你们出于怎样的好意,我也不能留,我要回去。虽然那个时候我知道回来并不一定能当上什么教授,不是那么容易做研究工作,但由于这两个诺言,我是非回来不可的,待不住了。不然的话,我在那儿并不是找不到女朋友。